ŃĆɵ¢ćķØ®ÕÄåÕÅ▓’╝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Ķ┐ÉÕŖ©Õ¦ŗµ£½ŃĆæ’Į×ķŁüń£üÕ▒▒Õ»©
ĶÆÖÕ¤ÄĶĆüÕ╝Ą-101698 02/07 30654.0/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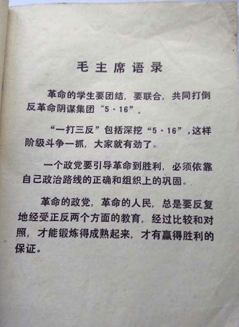
µĖģµ¤ź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ÅŹķØ®ÕæĮķøåÕ£śķüŗÕŗĢ’╝īµÖéķ¢ōĶĘ©Õ║”ÕŠłķĢĘ’╝īµĀ╣µōÜńÅŠÕ£©Õģ¼ÕĖāńÜäĶ│ćµ¢ÖķĪ»ńż║’╝īķĆÖÕ«īÕģ©Õ░▒µś»µīæÕŗĢńŠżń£Šµ¢ŚńŠżń£Š’╝īÕƤµ®¤Ķ┐½Õ«│µĢ┤õ║║ńÜäµö┐µ▓╗ķüŗÕŗĢ’╝īÕ«āµ│óÕÅŖÕģ©Õ£ŗ’╝īķĆĀµłÉńÜäĶ┐½Õ«│ĶłćÕåżÕüćķī»µĪłńöÜÕżÜńöÜÕ╗ŻŃĆé
ŃĆīµ¢ćķØ®µÖéµ£¤ŃĆŹµłæÕĘ▓Ķ©śõ║ŗ’╝īĶ”ŗĶŁēõ║åµē╣µ¢Śµ£ā’╝īńŠżń£ŠķĆĀÕÅŹµ┤ŠķøÖµ¢╣µŁ”µ¢ŚÕĀ┤µÖ»’╝īńöÜĶć│µ£ēõĖƵ¼ĪĶó½Õø░Õ£©µłæµ»ŹĶ”¬Õ¢«õĮŹńÅŠÕĀ┤’╝īĶ”¬ń£╝ńø«ńØ╣µŁ”µ¢ŚńÅŠÕĀ┤ńÜäńē浫Ą’╝īµ£ēõĖƵ¼ĪķÉĄĶĘ»Õż¦µ©ōĶó½ń¬üńäČÕø┤µö╗’╝īµĢ┤ÕĆŗµŁ”µ¢Śµö╗ķś▓Õż¦µæ¤ķćīÕ░▒µłæõĖĆÕĆŗÕ░ÅÕŁ®’╝īĶ║▓Õ£©õĖĆķéŖĶ¦ÆĶÉĮÕüĘÕüĘń£ŗ’╝īńÅŠÕĀ┤Õż¦µ©ōķćīÕ╣│µÖ鵳æń£╝õĖŁńÜäõ╝»õ╝»ŃĆüÕÅöÕÅöŃĆüķś┐Õ¦©ŃĆüÕż¦ÕōźÕōźŃĆüÕż¦Õ¦ÉÕ¦ÉÕĆæ’╝īķĆÖÕĆŗµÖéÕĆÖµś»ńé║õ║åĶ欵łæõ┐ØĶŁĘĶłćĶć¬ĶĪø’╝īõ╗¢ÕĆæńÜäÕŗćńīøÕ£śńĄÉń▓Šńź×’╝īõ║ÆńøĖķģŹÕÉłõ┐ØĶŁĘµł░µ¢ŚńÜäń▓Šńź×’╝īÕŠ×Õ░ÅÕ░▒µĘ▒µĘ▒µżŹÕģźõ║åµłæńÜäĶģ”µĄĘŃĆéķĆÖõ╣¤µś»ķÉĄĶĘ»µāģńĄÉńÜäńö▒õŠå’╝īµ¢ćķØ®µÖéµ£¤ķÉĄĶĘ»ÕŁÉÕ╝¤µŖ▒Õ£śÕ░ŹÕż¢ķó©µ░ŻńøøĶĪī’╝īÕÅ»õ╗źĶ¬¬µś»ķÉĄĶĘ»ÕŁÉÕ╝¤ÕŁĖµĀĪńÜäŃĆīµĀĪķó©µĀĪĶ©ōŃĆŹ’╝īµłæÕĆæńÜäÕż¦ÕōźÕż¦Õ¦ÉÕ░▒µś»ķĆÖµ©ŻÕĖČĶæŚµłæÕĆæĶĄ░ķĆ▓µ▒¤µ╣¢’╝īĶĆīµłæÕĆæĶĄ░ķĆ▓ńżŠµ£āÕÉÄ’╝īõ╣¤ÕÉīµ©Żµś»ķĆÖµ©ŻńÜäµģŗÕ║”õ┐ØĶŁĘµłæÕĆæńÜäķÉĄĶĘ»Õ░ÅÕ╝¤Õ╝¤Õ░ÅÕ”╣Õ”╣ÕĆæŃĆé
µłæÕ░Ź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ķüŗÕŗĢńÜäĶ©śµåČ’╝īµś»ÕŹ░Ķ▒ĪõĖŁµ¤ÉõĖĆÕż®µÖÜķŻ»ńłĖńłĖµ»öÕ╣│ÕĖĖÕø×õŠåńÜäĶ”üµÖÜ’╝īÕøĀńé║ńłĖńłĖõĖŹÕø×Õ«Č’╝īµłæÕĆæµś»õĖŹķ¢ŗķŻ»ńÜäŃĆéńłĖńłĖÕø×Õ«ČÕÉĵłæÕĆæÕø┤µĪīÕÉāķŻ»’╝īÕ░▒ĶüĮńłĖńłĖÕ░ŹÕ¬ĮÕ¬ĮĶ¬¬’╝īĶ¬░Ķ¬░Ķ¬░ŃĆüķÉĄĶĘ»Õ£░ÕŹĆÕÉ䵫ĄķāĮÕ«ŻÕĖāµŖō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łåÕŁÉ’╝īÕ£░ÕŹĆńĖĮķā©ŃĆüÕĘźÕŗÖµ«ĄŃĆüķø╗ÕŗÖµ«Ą’╝īĶ╗ŖÕŗÖµ«ĄŃĆüµ®¤ÕŗÖµ«Ąµ¤Éµ¤Éµ¤ÉķāĮĶó½µŖōõ║å’╝īµś»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łåÕŁÉ’╝īÕøĀńé║µÅÉÕł░ńÜ䵤Éõ║øõ║║ÕÉŹ’╝īÕ¬ĮÕ¬ĮÕŠłÕÉāķ®ÜÕ░ÅĶü▓Ķ¬¬’╝ܵĆÄõ╣łõ╗¢õ╣¤µś»’╝¤µÅÉÕł░ńÜäõ║║µłæõ╣¤µ£ēÕŹ░Ķ▒Ī’╝īõ╣¤µØźĶ┐浳æõ╗¼Õ«ČÕÉāĶ┐ćķźŁ’╝īÕ░ÅÕŁ®õ╣¤õĖŹµĢóÕżÜÕĢÅ’╝īõĮåÕŹ░Ķ▒ĪµĘ▒Õł╗ŃĆé
’Į×ķŁüń£üÕ▒▒Õ»©┬ĘķŁüń£üĶĆüÕ╝Ą



ŃĆÉ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ÅŹÕ橵ü®µØźõ║ŗõ╗ČÕÅæńö¤ÕēŹÕÉÄŃĆæ
’Į×ķŁüń£üÕ▒▒Õ»©┬ʵĩĶŹÉ’╝łÕø×ķĪŠÕÄåÕÅ▓’╝ē
Ķ┐ÉÕŖ©ń«Ćõ╗ŗ’╝Ü
ŌĆ£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ÅŹķØ®ÕæĮķøåÕøóŌĆØĶ┐ÉÕŖ© ŌĆØ
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’╝īµś»µīć1967Õ╣┤õĖŁÕ£ŗÕīŚõ║¼õĖĆÕ║”ÕŁśÕ£©õĖĆõĖ¬ÕÉŹõĖ║ķ”¢ķāĮõ║öõĖĆÕģŁń║óÕŹ½ÕģĄÕøóńÜäµ×üÕĘ”ń╗äń╗ć’╝īÕł®ńö©õ║ö┬ĘõĖĆÕģŁķĆÜń¤źµĢŻÕÅæÕÅŹÕ»╣Õ橵ü®µØźńÜäõ╝ĀÕŹĢŃĆéÕÉÄ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£©Õģ©ÕøĮĶīāÕø┤ÕåģÕ╝ĆÕ▒Ģ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Ķ┐ÉÕŖ©’╝īń«Ćń¦░µ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’╝īµĢ░õ╗źńÖŠõĖćĶ«ĪńÜäÕ╣▓ķā©ńŠżõ╝ŚķüŁÕł░Ķ┐½Õ«│ŃĆéµ£ēÕŁ”ĶĆģõ╝░Ķ«ĪÕÅŚÕł░µĖģµ¤źńÜäõ║║õ╗źÕŹāõĖćĶ«Ī’╝īµĢ┤µŁ╗õ║║õ╗ź10õĖćĶ«ĪŃĆé
1967Õ╣┤7µ£ł1µŚź’╝īÕīŚõ║¼Õż¢Ķ»ŁÕŁ”ķÖóµłÉń½ŗõ║åÕÉŹõĖ║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ńÜäń║óÕŹ½ÕģĄńŠżõ╝Śń╗äń╗ć’╝īÕ£©µłÉń½ŗÕż¦õ╝ÜõĖŖķĆÜĶ┐ćõ║åŃĆŖķ”¢ķāĮ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ń║óÕŹ½ÕģĄÕøóń¼¼õĖĆÕ▒Ŗõ╗ŻĶĪ©Õż¦õ╝ÜÕå│Ķ««ŃĆŗ’╝īÕģČõĖŁÕ░åÕ橵ü®µØźń¦░õĖ║ŌĆ£õĖŁÕøĮµ£ĆÕż¦ńÜäÕÅŹķØ®ÕæĮõĖżķØóµ┤Š’╝īµś»õĖŁÕøĮµ£ĆÕż¦ńÜäÕŹ¢ÕøĮõĖ╗õ╣ēĶĆģ’╝īõ┐«µŁŻõĖ╗õ╣ēĶĆģ’╝īÕÅ│ÕĆŠµ£║õ╝ÜõĖ╗õ╣ēĶĆģõ╣ŗõĖĆŌĆØ’╝īÕ╣Čń¦░õ╗¢õĖ║ŌĆ£µłæÕøĮÕģÜÕåģÕć║ńÄ░ńÜäõĖĆĶéĪĶĄäµ£¼õĖ╗õ╣ēµÜŚµĄüńÜäµĆ╗ÕÉÄÕÅ░õ╣ŗõĖĆŌĆØŃĆüŌĆ£õĖŁÕøĮń¼¼õ║īõĖ¬ĶĄ½ķ▓üµÖōÕż½Õ╝ÅńÜäõĖ¬õ║║ķćÄÕ┐āÕ«ČŌĆØŃĆé
1968Õ╣┤ÕÉÄńÜäõĖŁÕøĮ’╝īÕåŹõ╣¤µ▓Īµ£ēÕć║ńÄ░Ķ┐ćÕż¦Ķ¦äµ©ĪńÜäŌĆ£ń髵ēōÕ橵ü®µØźŌĆØńÜäĶĪīÕŖ©ŃĆéõĮåÕ£©ÕģŁÕŹüÕ╣┤õ╗Żµ£½Õ╝ĆÕ¦ŗńÜäµēĆĶ░ōŌĆ£µĖģńÉåķśČń║¦ķś¤õ╝ŹŌĆØõĖŁ’╝ī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ńÜäķŚ«ķóśĶó½ķ揵¢░µÅÉõ║åÕć║µØź’╝ī1970Õ╣┤1µ£ł24µŚź’╝īµ×ŚÕĮ¬ŃĆüµ▒¤ķØÆńŁēõ║║Õ£©õ║║µ░æÕż¦õ╝ÜÕĀéÕżÕ╝ĆÕż¦õ╝Ü’╝īÕ░▒µŖō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ķŚ«ķóśõĮ£õ║åŌĆ£µ¢░ńÜäµīćńż║ŌĆØŃĆéµ×ŚÕĮ¬Õż¦ÕŻ░ń¢ŠÕæ╝’╝ÜõĖŹÕÉāķźŁ’╝īõĖŹńØĪĶ¦ē’╝īõ╣¤Ķ”üµŖŖ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Į╗Õ║ĢµÉ×Õć║µØźŃĆéµ▒¤ķØÆĶ»┤’╝ÜÕź╣õĖēÕż®µ▓ĪńØĪĶ¦ēõ║å’╝īÕż¦ÕŻ░Õæ╝ÕŽĶ”üÕĮ╗Õ║ĢµĖģµ¤ź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ŃĆéĶć│µŁż’╝īµēĆĶ░ō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łåÕŁÉŌĆØÕĘ▓Õ╗Čõ╝ĖµłÉõĖ║õĖĆÕłćÕÅŹÕ»╣µł¢µĆĆń¢æõĖŁÕģ▒õĖŖÕ▒éķóåÕ»╝ÕÅŖÕÉäń║¦µ¢░ńö¤µö┐µØāńÜäõ║║µ░æńŠżõ╝ŚŃĆé1971Õ╣┤2µ£ł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Õ£©õĖĵ׌ÕĮ¬ńÜäõĖŖÕ▒éµö┐µ▓╗µ¢Śõ║ēõĖŁõĖÄÕ橵ü®µØźĶüöµēŗ’╝īõĮ┐ŌĆ£µĖģµ¤źõ║ö┬ĘõĖĆÕģŁĶ┐ÉÕŖ©ŌĆصŁŻÕ╝ŵē®Õż¦Õł░Õģ©õĖŁÕøĮĶīāÕø┤ŃĆé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2µ£ł8µŚźÕå│Õ«Ü’╝ī3µ£ł27µŚźÕÅæÕć║ķĆÜń¤ź’╝īń╗ŵ»øµ│ĮõĖ£µē╣ÕćåµłÉń½ŗ ŌĆ£ĶüöÕÉłõĖōµĪłń╗äŌĆØ’╝īÕ£©Õģ©ÕøĮÕż¦µŖōÕÅŹķØ®ÕæĮŃĆéĶ┐ÖõĖĆĶ┐ÉÕŖ©µīē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ŌĆ£õ║ī┬ĘÕģ½Õå│Õ«ÜŌĆØÕÆīŌĆ£õĖē┬Ęõ║īõĖāķĆÜń¤źŌĆØń▓Šńź×’╝īķććÕÅ¢õ╗źÕŠĆŌĆ£Õ«ĪÕ╣▓Õå│Õ«ÜŌĆØõĖŁńÜäń¦Źń¦ŹķĆ╝õŠøõ┐ĪÕüܵ│Ģ’╝īĶ»ĖÕ”éŌĆ£ÕØ”ńÖĮĶ┐ÉÕŖ©ŌĆØŃĆüŌĆ£õĖĆĶł¼ÕÅĘÕżŌĆØŃĆüŌĆ£õĖ¬Õł½ń¬üńĀ┤ŌĆØŌĆ”ŌĆ”µŖŖµĢóõ║ÄŌĆ£ńŖ»õĖŖõĮ£õ╣▒ŌĆØńÜäķĆĀÕÅŹµ┤Š’╝īÕ░żÕģȵś»ķ”¢ķāĮÕ£░Õī║ńÜäķĆĀÕÅŹµ┤Šń¤źĶ»åÕłåÕŁÉÕćĀõ╣ÄõĖĆÕż£õ╣ŗķŚ┤Õģ©ķā©µĢ┤µłÉõ║å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łåÕŁÉŌĆØŃĆ鵏«ÕŹüÕłåõ┐ØÕ«łńÜäõ╝░Ķ«Ī’╝īĶ┐ÖõĖĆĶ┐ÉÕŖ©ķāĮĶ┐½Õ«│õ║åÕćĀÕŹüõĖćńŠżõ╝Ś’╝īõĮ┐µĢ░õĖ浌ĀĶŠ£ńÜäńŠżõ╝Ś’╝īÕ░żÕģȵś»ń¤źĶ»åÕłåÕŁÉĶć┤µŁ╗Ķć┤µ«ŗŃĆéÕ”éÕÉīµ¢ćķØ®ÕÅ▓ńĀöń®ČĶĆģµēĆĶ©Ć’╝ÜŌĆ£Õ░▒Õģ©ÕøĮĶīāÕø┤ĶĆīĶ©Ć’╝īµĖģµ¤źŌĆś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ÖķŚ«ķóśõ║ŗÕ«×õĖŖÕ╣ČõĖŹµś»µĖģµ¤źķéŻõ║øµøŠń╗ÅÕ╝ĀĶ┤┤ÕÅŹÕ»╣Õ橵Ć╗ńÉåÕż¦ÕŁŚµŖźńÜäŌĆśķ”¢ķāĮń║óÕŹ½ÕģĄ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Ö’╝īĶĆīµś»ÕÅśµłÉõ║åÕ»╣õ║║µ░æõĖōµö┐ńÜäõĖĆń¦Źµēŗµ«ĄŃĆéńö▒õ║ÄÕÉäń¦ŹÕżŹµØéńÜäÕĤÕøĀ’╝īµĖģµ¤źŌĆś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ÖĶ┐ÉÕŖ©õĖĆńø┤µīüń╗ŁÕł░õĖĆõ╣ØõĖāÕģŁÕ╣┤ŌĆśÕøøõ║║ÕĖ«ŌĆÖÕĮ╗Õ║ĢÕ׫ÕÅ░ÕÉÄ’╝īµēŹõĖŹõ║åõ║åõ╣ŗŃĆé ŌĆØ
Ķ«®µłæõ╗¼ÕåŹÕø×Õł░1967Õ╣┤9µ£ł8µŚź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õĖ╗ÕĖŁÕ£©ŃĆŖõ║║µ░æµŚźµŖźŃĆŗÕÅæĶĪ©ńÜäզܵ¢ćÕģāŃĆŖĶ»äķÖČķōĖńÜäõĖżµ£¼õ╣”ŃĆŗõĖƵ¢ćõĖŁÕŖĀõ║åõĖƵ«ĄĶ»Ø’╝ÜŌĆ£ńÄ░Õ£©µ£ēõĖĆÕ░ŵƫÕÅŹķØ®ÕæĮÕłåÕŁÉõ╣¤ķććńö©õ║åĶ┐ÖõĖ¬ÕŖ×µ│Ģ’╝īõ╗¢õ╗¼ńö©Ķ▓īõ╝╝µ×üŌĆśÕĘ”ŌĆÖĶĆīÕ«×Ķ┤©µ×üÕÅ│ńÜäÕÅŻÕÅĘ’╝īÕł«ĶĄĘŌĆśµĆĆń¢æõĖĆÕłćŌĆÖńÜäÕ”¢ķŻÄ’╝īń髵ēō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’╝īµīæµŗ©ń”╗ķŚ┤’╝īµĘʵ░┤µæĖķ▒╝’╝īÕ”äµā│ÕŖ©µæćÕÆīÕłåĶŻéõ╗źµ»øõĖ╗ÕĖŁõĖ║ķ”¢ńÜ䵌Ā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’╝īĶŠŠÕł░ÕģČõĖŹÕÅ»ÕæŖõ║║ńÜäńĮ¬µüČńø«ńÜä’╝īµēĆĶ░ōŌĆś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ÖńÜäń╗äń╗ćĶĆģÕÆīµōŹń║ĄĶĆģ’╝īÕ░▒µś»Ķ┐ÖµĀĘõĖĆõĖ¬µÉ×ķś┤Ķ░ŗńÜäÕÅŹķØ®ÕæĮń╗äń╗ćŃĆéÕ║öõ║łõ╗źÕĮ╗Õ║ĢµÅŁķ£▓ŃĆéŌĆØŌĆ£Ķ┐ÖõĖ¬ÕÅŹķØ®ÕæĮń╗äń╗ćńÜäńø«ńÜ䵜»õĖżõĖ¬’╝īõĖĆõĖ¬µś»Ķ”üńĀ┤ÕØÅÕÆīÕłåĶŻéõ╗źµłæõ╗¼ńÜäõ╝¤Õż¦ķóåĶó¢µ»øõĖ╗ÕĖŁõĖ║ķ”¢ńÜäÕģÜõĖŁÕż«ńÜäķóåÕ»╝’╝øõĖĆõĖ¬µś»Ķ”üńĀ┤ÕØÅÕÆīÕłåĶŻé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Ėōµö┐ńÜäõĖ╗Ķ”üµö»µ¤▒ŌĆĢõ╝¤Õż¦ńÜäõĖŁÕøĮõ║║µ░æĶ¦ŻµöŠÕåøŃĆéŌĆØń¼¼õĖƵ¼ĪÕģ¼Õ╝ĆÕ£©µŖźÕłŖõĖŖµÅÉÕć║Ķ”üÕ£©Õģ©ÕøĮÕĮ╗Õ║ĢµÅŁķ£▓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ŌĆØŃĆé
1968Õ╣┤’╝īõĖŁÕż«µłÉń½ŗ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ĖōµĪłķóåÕ»╝Õ░Åń╗ä’╝īķÖłõ╝»ĶŠŠ’╝łÕÉÄĶó½ÕłŚõĖ║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ńÜäµōŹń║ĄĶĆģ’╝ēõ╗╗ń╗äķĢ┐’╝īÕģ¼Õ«ēķā©Õē»ķā©ķĢ┐µØÄķ£ćõĖ║ÕŖ×Õģ¼Õ«żõĖ╗õ╗╗’╝īĶ░óÕ»īµ▓╗ŃĆüÕÉ┤µ│ĢÕ«¬õĖ║ķóåÕ»╝Õ░Åń╗䵳ÉÕæśŃĆé
1970Õ╣┤1µ£ł31µŚź’╝ī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ÅæÕć║ŃĆŖÕģ│õ║ĵēōÕć╗ÕÅŹķØ®ÕæĮńĀ┤ÕØŵ┤╗ÕŖ©ńÜäµīćńż║ŃĆŗ ’╝īĶ┐øõĖƵŁźÕ£©Õģ©ÕøĮÕż¦Ķ¦äµ©ĪÕ£░Õ╝ĆÕ▒Ģ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┐ÉÕŖ©ŃĆé3µ£ł27µŚź’╝ī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ÅæÕć║ŃĆŖ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ģ│õ║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ńÜäķĆÜń¤źŃĆŗŃĆéķĆÜń¤źĶ»┤’╝ÜŌĆ£ÕøĮÕåģÕż¢ķśČń║¦µĢīõ║║ÕÉīµłæõ╗¼ńÜäµ¢Śõ║ēµś»ÕŠłÕżŹµØéńÜä’╝īÕÅŹķØ®ÕæĮń¦śÕ»åń╗äń╗ćÕå│õĖŹµś»ÕŬµ£ēõĖĆõĖ¬ŌĆś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ÖŌĆØ’╝īÕ£©Õģ©ÕøĮĶīāÕø┤ÕåģÕ╝ĆÕ▒Ģõ║å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ŌĆØĶ┐ÉÕŖ©ŃĆé10µ£ł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õĮ£Õć║µē╣ńż║’╝ÜŌĆ£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ķŚ«ķóśõĖŹĶāĮõĖĆķŻÄÕÉ╣’╝īµ£ēõ║øÕŹĢõĮŹÕĘ▓ń╗ÅõĖĆķŻÄÕÉ╣õ║å’╝īõŠŗÕ”éÕż¢Ķ»ŁÕŁ”ķÖóŃĆéŌĆØ
1971Õ╣┤2µ£ł8µŚź’╝īń╗ŵ»øµ│ĮõĖ£µē╣Õćå’╝ī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ÅæÕć║ŃĆŖÕģ│õ║ÄÕ╗║ń½ŗŌĆś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ÖõĖōµĪłĶüöÕÉłÕ░Åń╗äńÜäÕå│Õ«ÜŃĆŗŃĆéõĖōµĪłĶüöÕÉłÕ░Åń╗äõ╗źÕÉ┤ÕŠĘõĖ║ń╗äķĢ┐’╝īµØÄķ£ćõĖ║Õē»ń╗äķĢ┐’╝īń╗äÕæśµ£ē13õ║║ŃĆéŃĆŖÕå│Õ«ÜŃĆŗµīćÕć║’╝ÜÕ£©µĖģµ¤źĶ┐ćń©ŗõĖŁŌĆ£Ķ”üķś▓µŁóµē®Õż¦Õī¢’╝īÕÅłõĖŹĶ”üõĖĆķŻÄÕÉ╣ŌĆØŃĆ鵣żÕÉÄ’╝ī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łåÕŁÉńÜäĶ┐ÉÕŖ©µø┤ÕŖĀŌĆ£µĘ▒Õī¢ŌĆØŃĆé
Ķ┐ÖÕ£║µĖģµ¤źĶ┐ÉÕŖ©õĖĆńø┤µīüń╗ŁÕł░1974Õ╣┤µē╣µ×Śµē╣ÕŁöĶ┐ÉÕŖ©’╝īõ╣ŗÕÉÄõĖŹõ║åõ║åõ╣ŗŃĆéµĖģµ¤źĶ┐ÉÕŖ©õĖŹõ╗ģõĖźķ揵ē®Õż¦Õī¢’╝īĶĆīõĖöµ╝öÕÅśµłÉÕģ©ÕøĮµĆ¦ńÜäõĖżµ┤ŠńŠżõ╝Śń╗äń╗ćÕż¦µĘʵłśŃĆé
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’╝īµś»µīć1967Õ╣┤õĖŁÕ£ŗÕīŚõ║¼õĖĆÕ║”ÕŁśÕ£©õĖĆõĖ¬ÕÉŹõĖ║ķ”¢ķāĮõ║öõĖĆÕģŁń║óÕŹ½ÕģĄÕøóńÜäµ×üÕĘ”ń╗ä
ÕŹüÕ╣┤ÕŖ©õ╣▒µ£¤ķŚ┤’╝īÕÅæńö¤Ķ┐ćõĖƵĪ®ķ£ćµāŖÕģ©ÕøĮńÜäÕż¦µĪł’╝īĶ┐ÖÕ░▒µś»µēĆĶ░ōŃĆŖ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 ÕæĮķøåÕøóµĪłŃĆŗŃĆéĶ┐ÖµĪ®Õģ¼µĪłĶĄĘµ║Éõ║Ä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ÅŹÕ橵ü®µØźńÜäõ║ŗõ╗ČŃĆé
ń¼öĶĆģµś»ÕĮōµŚČ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Ŗ×õ║ŗń╗äńÜäÕĘźõĮ£õ║║Õæś’╝ī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µĆ╗ ńÉåõ║ŗõ╗ČÕÅæńö¤µŚČńÜäĶ¦üĶ»üõ║║ŃĆé
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”üĶ┤┤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µĆ╗ńÉåńÜäÕż¦ÕŁŚµŖź’╝īÕż¦ń║”ÕÅæńö¤Õ£© 1967 Õ╣┤ 8 µ£łõĖŖ µŚ¼ŃĆéµ£ĆµŚ®ÕÅæńÄ░Ķ┐Öõ╗Čõ║ŗÕ░åĶ”üÕÅæńö¤ńÜ䵜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Ķ«░ĶĆģń½ÖńÜäõĖĆõĮŹķĆÜĶ«»ÕæśŃĆéĶ┐ÖõĮŹķĆÜĶ«»Õæś ÕĮōµŚČµŁŻÕ£©ÕīŚõ║¼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ķććĶ«┐’╝īõ╗¢Õ»╣ÕīŚõ║¼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ÕÉäµ┤ŠÕł½ÕÆīõ╗¢õ╗¼ńÜäÕż┤Õż┤ķāĮµ»öĶŠāńå¤ µéē’╝īÕøĀµŁżÕÉäµ┤ŠÕż┤Õż┤ńÜäĶ¦éńé╣ÕÆīĶ┐ÉÕŖ©õĖŁńÜäĶĪīÕŖ©Ķ«ĪÕłÆķāĮõĖŹķü┐Ķ«│õ╗¢ŃĆé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 ÕģĄÕøóŌĆصś»õĖĆõĖ¬ÕŠłÕ░ÅńÜäńŠżõ╝Śń╗äń╗ć’╝īÕ«āńÜäĶĪīÕŖ©Õ░Įń«ĪÕĮ▒ÕōŹõĖŹõ║åÕż¦Õ▒Ć’╝īõĮåÕŹ┤õ╗ŻĶĪ©õ║åÕĮōµŚČ ńÜäõĖĆń¦Źµ×üÕĘ”µĆصĮ«’╝īõ╗¢õ╗¼µā│ÕģģÕĮō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ńÜäµĆźÕģłķöŗŃĆé
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ģ¼Õ╝ĆĶ┤┤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µŖź’╝īµŁŻµś»Ķ┐ÄÕÉłõ║å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ńÜäÕ┐āķćī µā│ÕüÜĶĆīõĖŹµĢóÕüÜńÜäõ║ŗ’╝īõĮåµś»Ķ┐Öõ║øń║óÕŹ½ÕģĄķöÖĶ»»Õ£░õ╝░Ķ«Īõ║åÕĮóÕŖ┐’╝īŌĆ£ķĆĀÕÅŹŌĆص£¬µłÉ’╝īÕŹ┤µłÉ õ║åÕÅŹķØ®ÕæĮŃĆé
µŹ«ÕĮōõ║ŗõ║║Õø×Õ┐å’╝Ü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Ł¢ÕłÆ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’╝īĶ”üÕģ¼Õ╝ĆĶ┤┤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µŖźńÜäõ╝ÜĶ««ÕÆīÕćåÕżć Ķ┐ćń©ŗĶó½Ķ┐ÖõĮŹķĆÜĶ«»ÕæśÕģ©ķā©µÄīµÅĪŃĆ鵏«Ķ»┤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╝Ćõ╝ܵŚČõ╗¢õ╣¤Õ£©Õ£║’╝īµēĆõ╗źŌĆ£õ║ö 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ÜäĶĪīÕŖ©Ķ«ĪÕłÆ’╝īÕīģµŗ¼Ķ┤┤Õż¦ÕŁŚµŖźńÜ䵌ČķŚ┤ŃĆüÕ£░ńé╣ŃĆüĶĪīÕŖ©µŁźķ¬ż’╝īÕż¦ÕŁŚµŖźńÜäµĀć ķóśńŁē’╝īÕ£©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╝ĆÕ¦ŗĶĪīÕŖ©ÕēŹńÜäÕøøŃĆüõ║öõĖ¬Õ░ŵŚČ’╝īĶ┐ÖõĮŹķĆÜĶ«»ÕæśÕ░▒Õ░åµāģÕåĄÕÅŖ µŚČÕćåńĪ«Õ£░µŖźÕæŖõ║åõĖŁÕż«µ¢ćķØ®Ķ«░ĶĆģń½ÖŃĆéÕ”éµ×£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µā│Ķ”üÕłČµŁóĶ┐ÖõĖ¬õ║ŗõ╗ČńÜäÕÅæńö¤ ’╝īµ£ēÕģģÕłåńÜ䵌ČķŚ┤ŃĆéńäČĶĆī’╝ī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ÕŹ┤µöŠń║Ą’╝īµĆéµü┐Ķ┐ÖõĖ¬µ£¼ÕÅ»õ╗źķü┐ÕģŹńÜäõ║ŗõ╗ČŃĆé õ║ŗÕÉÄ’╝īµ▒¤ķØÆÕŹ┤µŖŖĶ┐ÖõĖ¬ńĮ¬Ķ┤ŻõĖĆÕÅżĶäæÕä┐Õ£░µĀĮÕł░ÕŹ│Õ░åµēōÕĆÆńÜäĶ┐ćÕÄ╗ńÜäÕÉīõ╝ÖńÜäĶ║½õĖŖŃĆé
õ║ŗµāģńÜäń╗ÅĶ┐浜»Ķ┐ÖµĀĘńÜä:1967 Õ╣┤ 8 µ£łõĖŖµŚ¼ńÜäõĖĆõĖ¬µÖÜõĖŖ 9 ńé╣ÕĘ”ÕÅ│’╝īõĖŁÕż«µ¢ćķØ®Ķ«░ ĶĆģń½ÖÕīŚõ║¼Ķ«░ĶĆģń╗äĶ┤¤Ķ┤Żõ║║ĶóüÕģēÕ╝║’╝īń╗Öµłæµēōõ║åõĖĆõĖ¬ń┤¦µĆźńöĄĶ»Ø’╝īĶ»┤µ£ēķćŹĶ”üµāģÕåĄµŖźÕæŖŃĆé õ╗¢Õ£©ńöĄĶ»ØõĖŁĶ»┤:ÕīŚõ║¼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µ£ēõĖ¬ÕŽ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ÜäńŠżõ╝Śń╗äń╗ć’╝īńŁ¢ÕłÆõ║åõĖĆĶĄĘ 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ńÜäµ┤╗ÕŖ©ŃĆéõ╗¢õ╗¼Õå│Õ«Üõ╗ŖµÖÜķøȵŚČÕ£©ÕīŚõ║¼ńÜäµ¢░ĶĪŚÕÅŻŃĆüĶź┐ÕŹĢŃĆüõĖ£ÕŹĢńŁēķŚ╣ÕĖéÕī║ Õż¦ĶĪŚõĖŖ’╝īÕ╝ĀĶ┤┤µö╗Õć╗Õ橵Ć╗ńÉåńÜäÕż¦ÕŁŚµŖź’╝īÕż¦ÕŁŚµŖźÕĘ▓ń╗ÅÕåÖÕźĮ’╝īÕŬńŁēÕł░Õż£µĘ▒õ║║ķØÖńÜ䵌ČÕĆÖ Õć║ÕÄ╗Õ╝ĀĶ┤┤ŃĆéĶóüÕģēÕ╝║Ķ┐śĶ»┤õ║åÕćĀÕ╝Āµö╗Õć╗Õ橵Ć╗ńÉåÕż¦ÕŁŚµŖźńÜäµĀćķóśŃĆéõ╗¢Õ╝║Ķ░āĶ┐ÖõĖ¬µāģÕåĄµś»Õćå ńĪ«ńÜä’╝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Ł¢ÕłÆĶ┐ÖõĖ¬ĶĪīÕŖ©’╝īµłæõ╗¼ńÜäķĆÜĶ«»ÕæśÕ░▒Õ£©ńÄ░Õ£║’╝īÕĖīµ£øķ®¼õĖŖÕÉæ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µ▒ćµŖźŃĆé ÕĮōµŚČ’╝ī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䵣ŻÕ£©ķÆōķ▒╝ÕÅ░ÕŹüÕģŁµź╝Õż¦õ╝ÜĶ««Õ«żÕ╝Ćõ╝ÜŃĆé
µłæµŖŖĶóüÕģēÕ╝║µŖźÕæŖńÜäÕåģÕ«╣µĢ┤ńÉåµłÉńöĄĶ»ØĶ«░ÕĮĢ’╝īÕł░õ╝ÜÕ£║ńø┤µÄźµēŠõĖ╗ń«ĪÕŖ×õ║ŗń╗äńÜäÕ░Åń╗䵳ÉÕæśµłÜµ£¼ń”╣’╝īµŖŖńöĄĶ»ØĶ«░ ÕĮĢķĆüń╗Öõ╗¢ń£ŗ’╝īõ╗¢ń£ŗÕÉÄÕŬĶ»┤õ║åõĖĆÕÅź:ŌĆ£Ķ»ĘĶ░óÕ»īµ▓╗ÕÉīÕ┐ŚÕżäńÉå!ŌĆص£¬õĮ£µē╣ńż║Õ░▒µŖŖńöĄĶ»Ø Ķ«░ÕĮĢķĆÆń╗Öµłæ’╝īµłæĶĆāĶÖæµłÜµ£¼ń”╣ńÜäĶ»Øń®║ÕÅŻµŚĀÕ棒╝īµłæµēŠĶ░óÕ»īµ▓╗õĖŹÕźĮĶ»┤’╝īõ║ĵś»µłæÕ£©ńöĄĶ»Ø Ķ«░ÕĮĢń║ĖńÜäµē╣ńż║µĀÅÕåÖõĖŖ:ŌĆ£µłÜµ£¼ń”╣ÕÉīÕ┐ŚĶ»┤’╝īµŁżõ║ŗĶ»ĘĶ░óÕ»īµ▓╗ÕÉīÕ┐ŚÕżäńÉåŃĆéŌĆØńäČÕÉĵöŠÕ£© µŁŻÕ£©ÕłŚÕĖŁ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õ╝ÜńÜäĶ░óÕ»īµ▓╗ķØóÕēŹ’╝īµłæÕ░▒ķĆĆÕć║õ╝ÜÕ£║ŃĆé
µīēĶ░óÕ»īµ▓╗ÕĮōµŚČńÜäĶ║½õ╗Į’╝īµłÜµ£¼ń”╣Ķ«®Ķ░óÕ»īµ▓╗ÕÄ╗ÕżäńÉå’╝īõ╝╝õ╣Äõ╣¤ķĪ║ńÉåµłÉń½Ā’╝īĶ░óÕ»īµ▓╗ µś»õĖŁÕż«µö┐µ▓╗Õ▒ĆÕĆÖĶĪźÕ¦öÕæśŃĆüÕøĮÕŖĪķÖóÕē»µĆ╗ńÉå’╝īÕīŚõ║¼ÕĖéķØ®ÕæĮÕ¦öÕæśõ╝ÜõĖ╗õ╗╗ŃĆüÕģ¼Õ«ēķā©ķā©ķĢ┐ ŃĆéõ╗ĵłæµŖŖńöĄĶ»ØĶ«░ÕĮĢµöŠÕ£©Ķ░óÕ»īµ▓╗ķØóÕēŹÕł░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╝ĀĶ┤┤ÕÅŹ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µŖź’╝ī Ķć│Õ░æĶ┐śµ£ēõĖżŃĆüõĖēõĖ¬Õ░ŵŚČ’╝īÕÅ»µś»ńø┤Õł░ 12 ńé╣ÕÉÄ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õ╝ÜĶ««µĢŻõ╝Ü’╝īÕŖ×õ║ŗń╗äÕĆ╝ńÅŁ Õ«żõĖĆńø┤ńŁēÕŠģÕżäńÉåĶ┐Öõ╗Čõ║ŗµāģńÜäµē╣ńż║ķāĮµ▓Īµ£ēÕŠŚÕł░ńŁöÕżŹŃĆéÕÉÄµØź’╝īµłæÕɼĶ»┤’╝īÕÅéÕŖĀõ╝ÜĶ««ńÜä Õ░Åń╗䵳ÉÕæśÕÆīÕłŚÕĖŁõ║║ÕæśķāĮÕ£©õ╝ÜÕ£║õ╝Āń£ŗõ║åĶ┐ÖõĖ¬ńöĄĶ»ØĶ«░ÕĮĢ’╝īÕĮōµÖܵĢŻõ╝ÜÕÉÄ’╝īÕ░Åń╗䵳ÉÕæśÕÆī ÕŠĆÕĖĖõĖƵĀĘ’╝īõ╝╝õ╣Äõ╗Ćõ╣łõ║ŗµāģķāĮµ▓Īµ£ēÕÅæńö¤ŃĆéÕĮōńäČõ╣¤µ▓Īµ£ēķććÕÅ¢õ╗╗õĮĢķóäķś▓µÄ¬µ¢ĮŃĆé
ÕŹłÕż£ÕÉÄ’╝īńö▒õ║Ä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ńÜäµöŠń║Ą,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┤┤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µŖźńÜäõ║ŗ õ╗Čń╗łõ║ÄÕÅæńö¤õ║åŃĆéÕÉÄÕŹŖÕż£’╝īµłæµēōńöĄĶ»ØķŚ«ÕīŚõ║¼ÕŹ½µłŹÕī║ÕÅĖõ╗żÕæśÕéģÕ┤ćńó¦ńÜäń¦śõ╣”ķéĄÕ┤ćÕŗ浜» ÕÉ”µÄīµÅĪõ║å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┤┤Õ橵Ć╗ńÉåÕż¦ÕŁŚµŖźńÜäµāģÕåĄ’╝īõ╗¢ÕæŖĶ»ēµłæÕĘ▓ń╗ŵÄīµÅĪõ║å’╝īŌĆ£õ║ö 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┤┤Õć║Õż¦ÕŁŚµŖźÕÉÄ’╝īķ®¼õĖŖÕ░▒µ£ēõ║║ńö©ÕģČÕ«āÕåģÕ«╣ńÜäÕż¦ÕŁŚµŖźĶ”åńø¢õĖŖõ║åŃĆéõĖ║õ║åĶ»ü Õ«×ķéĄÕ┤ćÕŗćµēĆĶ»┤ńÜäµāģÕåĄ’╝īń¼¼õ║īÕż®µŚ®µÖ©’╝īÕŖ×õ║ŗń╗äńÜäń¤½ńÄēÕ▒▒ÕÆīÕ¦£µØÉńåÖõ╣śĶĮ”ÕÄ╗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 ÕģĄÕøóŌĆØĶ┤┤Õż¦ÕŁŚµŖźńÜäÕ£░µ¢╣ĶĮ¼õ║åõĖĆÕ£ł’╝īÕåŹµ▓Īµ£ēÕÅæńÄ░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µŖźŃĆé
Ķ┐ÖõĖ¬õ║ŗõ╗ČńÜäÕÅæńö¤’╝īµś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µöŠń║ĄńÜäń╗ōµ×£’╝īõ╗źÕĮōµŚČõĖŁÕż«µ¢ćķخգ©ń║óÕŹ½ÕģĄÕ┐āńø« õĖŁńÜäÕ£░õĮŹ’╝īÕłČµŁóĶ┐Öõ╗Čõ║ŗµāģÕÅæńö¤ÕÅ»õ╗źĶ»┤õĖŹĶ┤╣ÕÉ╣ńü░õ╣ŗÕŖø’╝īÕŬĶ”üÕł░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µēŠÕł░ŌĆ£õ║ö 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ÜäÕż┤Õż┤µēōõĖ¬µŗøÕæ╝’╝īĶ░ģõ╗¢õ╗¼õ╣¤õĖŹµĢóõĖƵäÅÕŁżĶĪī;Õ”éµ×£ń£¤ńÜäĶ»┤µ£ŹõĖŹõ║å’╝īĶ┐ś ÕÅ»õ╗źķććÕÅ¢Õ╝║ńĪ¼µÄ¬µ¢Į’╝īÕłČµŁóÕ«āńÜäÕÅæńö¤’╝īĶ┐ÖÕ£©Ķ┐ćÕÄ╗µś»µ£ēÕģłõŠŗńÜä(Õ”éÕ»╣Õż¢Ķ»ŁÕŁ”ķÖóńÜäÕłśõ╗ż Õć»)’╝īÕÅ»µś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ĖŹń«Ī’╝īµŖŖĶ┐Öõ╗Čõ║ŗµÄ©ń╗ÖĶ░óÕ»īµ▓╗ÕÄ╗ÕżäńÉåŃĆ鵏«µłæńÜäõ║åĶ¦Ż’╝īĶ░óÕ»īµ▓╗ĶÖĮ µ£ēķéŻõ╣łÕżÜÕ«śĶĪö’╝īõĮåÕ£©ķćŹÕż¦ķŚ«ķ󜵳¢µĢŵä¤ķŚ«ķóśõĖŖ’╝īõ╗¢ń╗ØõĖŹµĢóõĮ£Õå│Õ«Ü’╝īõ╗¢Ķ”üń£ŗõĖŁÕż«µ¢ć ķØ®ńē╣Õł½µś»Ķ”üń£ŗµ▒¤ķØÆńÜäĶäĖĶē▓ĶĪīõ║ŗńÜä’╝īõ╗¢ńÜäõĖŹõĮ£õĖ║’╝īõ╣¤õĖŹĶČ│õĖ║ÕźćŃĆé
µöŠń║Ą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┤┤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µŖźõĖŹµś»ÕüČńäČńÜä’╝īÕŬõĖŹĶ┐浜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 ń╗äÕ»╣Õ橵ü®µØźńÜäµĆüÕ║”ńÜäõĖƵ¼ĪĶĪ©µ╝öĶĆīÕĘ▓ŃĆ鵏«µłæÕ£©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Ŗ×õ║ŗń╗äÕĘźõĮ£µ£¤ķŚ┤ńÜäõ║åĶ¦Ż’╝ī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䵳ÉÕæśĶĪ©ķØóõĖŖõ╝╝õ╣ÄÕ»╣Õ橵ü®µØźµś»Õ░ŖķćŹńÜä’╝īńē╣Õł½µś»Õ£©Õģ¼Õ╝ĆÕ£║ÕÉł’╝īĶ┐ÖÕŬµś» ńÄ░Ķ▒ĪŃĆéĶ┐Öµś»ÕøĀõĖ║ÕĮōµŚČµ»øµ│ĮõĖ£Ķ”üõŠØķØĀÕ橵ü®µØźń«ĪńÉåÕģ½õ║┐õ║║ÕÅŻńÜäÕøĮÕ«Č’╝īµø┤õĖ╗Ķ”üńÜ䵜»Õæ© µü®µØźÕ£©ÕģÜŃĆüµö┐ŃĆüÕåøõĖŁ’╝īÕ£©õ║║µ░æńŠżõ╝ŚõĖŁńÜäÕ©üµ£ø’╝īńóŹõ║ÄĶ┐Öõ║ø’╝īÕŹ│õĮ┐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Õ»╣Õ橵ü® µØźÕ┐āµĆĆõĖŹµ╗Ī’╝īõ╣¤õĖŹµĢóĶĮ╗õĖŠÕ”äÕŖ©ŃĆéõĖ║õ║åń╗┤µŖżÕøĮÕ«ČńÜ䵣ŻÕĖĖĶ┐ÉõĮ£’╝īõ┐ØĶ»üõ║║µ░æńÜäĶĪŻķŻ¤õĮÅ ĶĪī’╝īÕ橵ü®µØźµŚźÕż£µōŹÕŖ│’╝īÕÉīµŚČÕÅłĶ”üÕÉīµ»øµ│ĮõĖ£µö»µīüńÜä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ÜäŌĆ£ķĆĀÕÅŹŌĆØ’╝īŌĆ£µēōÕĆÆ ŌĆØõĖĆÕłć’╝īõ┐صīüÕŹÅĶ░āŃĆéõĖŁÕż«µ¢ćķخգ©µ¢ćÕī¢ķØ®ÕæĮÕłØµ£¤’╝īÕŬĶ”üÕ╝Ćõ╝ÜķĆÜń¤źÕ橵ü®µØźÕÅéÕŖĀ’╝īõ╗¢ ķāĮÕł░õ╝ÜŃĆé1967 Õ╣┤õ╗źÕÉÄÕģÜõĖŁÕż«ÕÆīÕøĮÕŖĪķÖóńÜäÕż¦µē╣ķóåÕ»╝Õ╣▓ķā©Ķó½µēōÕĆÆ’╝īÕøĮÕ«Čµ£║Õģ│ķĆɵŁźńś½ ńŚ¬’╝īĶāĮÕć║µØźÕĘźõĮ£ńÜäµö┐µ▓╗Õ▒ĆÕ¦öÕæśÕÆīÕē»µĆ╗ńÉåÕ»źÕ»źµŚĀÕćĀ’╝īÕ橵ü®µØźńÜäµŗģÕŁÉÕ░▒ĶČŖµØźĶČŖķćŹŃĆé Ķ┐ÖµŚČõĖŁÕż«µ¢ćķخգ░õĮŹÕŹ┤µŚźńøŖÕŹćķ½ś’╝īÕ«āÕ«×ķÖģõĖŖõ╗Żµø┐õ║åõ╣”Ķ«░Õżä’╝īõĖŁÕż«ÕÉæÕģ©ÕøĮÕÅæµ¢ćõ╗ȵŖŖ 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ÆīÕģÜõĖŁÕż«ŃĆüÕøĮÕŖĪķÖóÕÆīõĖŁÕż«ÕåøÕ¦öÕ╣ČÕłŚ’╝īõĮ┐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ÅśµłÉõ║åµ£ēÕ«×µØāńÜäµö┐µ▓╗ ń╗äń╗ćŃĆé
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Õ»╣Õ橵ü®µØźńÜäµĆüÕ║”’╝īõ╗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õĖĆÕ╝ĆÕ¦ŗÕ░▒ĶĪ©ńÄ░Õć║µØź’╝īõĖ╗Ķ”üķøå õĖŁÕ£©õĖżõĖ¬ķŚ«ķóśõĖŖ:õĖƵś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Ķ”üŌĆ£ķĆĀÕÅŹŌĆØ’╝īĶ”üŌĆ£µēōńóĵŚ¦µ£║ÕÖ©ŌĆØ’╝īŌĆ£ńĀ┤ÕøøµŚ¦ŌĆØ ’╝īńģĮÕŖ©ń║óÕŹ½ÕģĄÕå▓Õć╗ÕøĮÕ«Čµ£║Õģ│’╝īńĀ┤ÕØŵŁŻÕĖĖńö¤õ║¦ÕÆīńö¤µ┤╗ń¦®Õ║Å’╝īĶĆīÕ橵ü®µØźÕ┐ģķĪ╗ń╗┤µŖżÕøĮ Õ«Čµ£║µ×äńÜ䵣ŻÕĖĖĶ┐ÉõĮ£’╝īÕÆīµŁŻÕĖĖńÜäÕĘźŃĆüÕå£õĖÜńŁēÕÉäķĪ╣ńö¤õ║¦ŃĆéõĖŁÕż«µ¢ćķØ®µł¢µśÄµł¢µÜŚÕ£░Õł░Õżä ńģĮķŻÄńé╣ńü½’╝īÕ橵ü®µØźÕÅ¬ÕźĮÕÄ╗Õć║ķØóµĢæńü½’╝īÕÄ╗Ķ»┤µ£Źń║óÕŹ½ÕģĄķĆĀÕÅŹõĖŹĶāĮńĀ┤ÕØÅńö¤õ║¦ÕÆīÕĘźõĮ£’╝ī ĶĆī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ÕłÖĶ»¼ĶöæÕ橵ü®µØźµś»ŌĆ£µĢæńü½ķś¤ķĢ┐ŌĆØŃĆéµ▒¤ķØƵøŠÕ£©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Ŗ×Õģ¼Õ«żÕĮōńØĆÕĘźõĮ£ õ║║ÕæśńÜäķØóĶ»┤:ŌĆ£µĆ╗ńÉåÕæĆ’╝īµĆ╗ńÉåÕæĆ’╝īµĆÄõ╣łµĆ╗ÕÄ╗ÕĮōµĢæńü½ķś¤ÕæĆ!ŌĆØõ║īµś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ģĮÕŖ© ń║óÕŹ½ÕģĄµēōÕĆÆÕÆīµÅ¬µ¢ŚÕż¦µē╣ĶĆüÕ╣▓ķā©’╝īĶĆīÕ橵ü®µØźÕłÖÕŹāµ¢╣ńÖŠĶ«Ī’╝īõ╗źÕÉäń¦Źµ¢╣Õ╝Åõ┐صŖżĶĆüÕ╣▓ķā© ;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Ķ«żõĖ║’╝īÕ橵ü®µØźµś»ŌĆ£ĶĆüõ┐ØŌĆØ’╝īµś»ń╗ÖńŠżõ╝ŚĶ┐ÉÕŖ©ŌĆ£µ│╝Õåʵ░┤ŌĆØŃĆéÕ橵ü®µØźÕÆīõĖŁ Õż«µ¢ćķØ®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Õ£©Ķ┐ÖõĖżõĖ¬õĖ╗Ķ”üķŚ«ķóśõĖŖõĖĆńø┤ÕŁśÕ£©ńØĆÕłåµŁ¦ŃĆéÕøĀµŁż’╝ī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Õ£©ÕåģÕ┐ā õĖŁõ╗ÄõĖŹµŖŖÕ橵ü®µØźÕĮōõĮ£ŌĆ£µŚĀõ║¦ķśČń╗ÖÕÅĖõ╗żķā©ŌĆØńÜäõ║║ŃĆé
Ķ┐ÖķćīõĖŠõĖżõĖ¬Õ░ÅõŠŗÕŁÉ:
1967 Õ╣┤ 2 µ£łÕÅæńö¤µēĆĶ░ōŌĆ£õ║īµ£łķĆåµĄüŌĆØÕÉÄ’╝ī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ń╝¢ĶŠæõĖĆń¦ŹÕŽŌĆ£µēōÕĆÆõĖĆ Õłć’╝īµĆĆń¢æõĖĆÕłćŌĆØńÜäĶĄäµ¢Ö’╝īõ╝üÕøŠĶ»┤µśÄõĖ╗Õ╝ĀŌĆ£µēōÕĆÆõĖĆÕłć’╝īµĆĆń¢æõĖĆÕłćŌĆØńÜäõĖŹµś»õĖŁÕż«µ¢ć ķØ®’╝īĶĆīµś»ķéŻõ║øµö╗Õć╗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Üäµö┐µ▓╗Õ▒ĆÕ¦öÕæśÕÆīÕē»µĆ╗ńÉåŃĆéÕ£©Ķ┐ÖõĖ¬µØɵ¢ÖõĖŁ’╝īõĮ£õĖ║µŁŻķØó ÕŁ”õ╣ĀńÜäµ¢ćõ╗ČõĖŁķĆēõ║åµ»øõĖ╗ÕĖŁŃĆüµ×ŚÕĮ¬ŃĆüķÖłõ╝»ĶŠŠŃĆüµ▒¤ķØÆńŁēõ║║Õģ│õ║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õĖŁĶ”üĶ«▓µö┐ ńŁ¢’╝īõĖŹõĖ╗Õ╝ĀµēōÕĆÆõĖĆÕłćńÜäĶ©ĆĶ«║ŃĆéĶĆīõĮ£õĖ║ÕÅŹķØóµØɵ¢ÖÕŖĀõ╗źµē╣ÕłżńÜäÕłÖķĆēõ║åķÖČķōĖŃĆüńÄŗõ╗╗ķćŹ ŃĆüķÖłµ»ģŃĆüĶ░Łķ£ćµ×ŚńŁēõ║║Õ£©µ¢ćķØ®õĖŁĶ«▓Ķ┐ćńÜäõĖ¬Õł½Ķ┐ćÕż┤Ķ»Øµł¢ķöÖĶ»ØŃĆéĶ┐ÖõĖżµ¢╣ķØóńÜäĶ©ĆĶ«║ķāĮµ▓Īµ£ēķĆēÕ橵ü®µØźńÜäĶ©ĆĶ«║’╝īõĮåµś»µ£ĆÕÉÄÕŹ┤ķĆüÕ橵ü®µØźµē╣ÕÅæĶ┐ÖõĖ¬µØɵ¢ÖŃĆé
ÕÅ”õĖĆõ╗Čõ║ŗµś» 1967 Õ╣┤ 6 µ£łÕłØ’╝īÕ£©õ║║µ░æÕż¦õ╝ÜÕĀéÕż¦ńż╝ÕĀéÕżÕ╝ĆõĖĆõĖ¬Õż¢õ║ŗÕÅŻńÜäÕż¦õĖōķÖó
µĀĪÕÉäµ┤Šń║óÕŹ½ÕģĄÕż¦õ╝Ü’╝īĶ┐ÖõĖ¬õ╝ÜÕĤµØźńÜäńø«ńÜ䵜»ÕŽ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ć║ķØóµē╣Ķ»äÕż¢õ║ŗÕÅŻÕż¦õĖōķÖóµĀĪ Õ░æµĢ░õ║║µŖŖµ¢Śõ║ēń¤øÕż┤Õ»╣ÕćåÕ橵Ć╗ńÉåŃĆüõ╝üÕøŠµēōÕĆÆÕ橵Ć╗ńÉåńÜäÕÅŹÕŖ©µĆصĮ«’╝īńäČĶĆīÕ£©Õż¦õ╝ÜõĖŖ’╝ī µ▒¤ķØÆõ╗źÕÅŖ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䵳ÉÕæśńÜäÕÅæĶ©Ć’╝īĶ©ĆõĖŹÕÅŖõ╣ē’╝īõĖŹńØĆĶŠ╣ķÖģĶ»┤õĖĆķĆÜ’╝īµ▓Īµ£ēõĖĆõĖ¬õ║║ Ķ»┤Õ橵ü®µØźµś»ŌĆ£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ŌĆØńÜäõ║║ŃĆéķÖłõ╝»ĶŠŠń¼¼õĖĆõĖ¬ÕÅæĶ©Ć’╝īõ╗¢ÕÅ»ĶāĮµē╣Ķ»äõ║嵤Éõ║ø µ┤ŠÕł½ńÜäµ×üÕĘ”µĆصĮ«ŃĆéõ╗¢Ķ«▓Õ«īÕÉÄ’╝īµ▒¤ķØÆĶ«▓Ķ»ØÕÅ»ĶāĮÕł║õ║åõĖĆõĖŗķÖłõ╝»ĶŠŠŃĆéķÖłõ╝»ĶŠŠÕÉōÕŠŚÕģŁńź× µŚĀõĖ╗’╝īµāŖµģīÕż▒µÄ¬’╝īń½¤ńäČõ╗ÄõĖ╗ÕĖŁÕÅ░õĖŖĶĘæÕł░ÕÉÄÕÅ░µØźÕø×ĶĖ▒µŁź’╝īõ╗¢ń£ŗÕł░µłæ’╝īķ®¼õĖŖµŖŖµłæÕŽ Õł░ÕÉÄõ╝æµü»ÕÄģķŚ©ÕÅŻķŚ«µłæ:ŌĆ£µłæńÜäĶ«▓Ķ»ØõĮĀÕɼõ║åµ£ēõ╗Ćõ╣łķŚ«ķóśÕÉŚ?ŌĆصłæńŁöÕżŹĶ»┤:ŌĆ£µłæµ▓Ī ÕɼÕć║µØźŃĆéŌĆØÕÉÄµØźõ╗¢ÕÅłķŚ«õ║åµłæõĖƵ¼ĪŃĆéÕö»ńŗ¼ÕłŚÕĖŁ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õ╝ÜńÜäÕÅČńŠż’╝īÕÅ»ĶāĮµ▓ĪµæĖ Õćåµ▒¤ķØÆńÜäĶäēµÉÅ’╝īĶ«▓õ║åõĖżÕÅźĶ»Ø:ŌĆ£µ×ŚÕĮ¬ÕÉīÕ┐Śµś»ÕŠłÕ░ŖķćŹÕ橵Ć╗ńÉåńÜäŌĆØ’╝īŌĆ£Õ橵Ć╗ńÉåµś»µŚĀ 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ńÜäÕśø!ŌĆØõ╗źÕÅČńŠżÕĮōµŚČńÜäĶ║½õ╗ĮÕÆīÕ£░õĮŹ’╝īÕź╣ńÜäĶ«▓Ķ»ØĶĄĘńÜäõĮ£ńö©µ£ēķÖÉ’╝īÕøĀ õĖ║Õź╣õĖŹń«Ś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Üäõ║║ŃĆéĶ┐ÖõĖ¬õ╝ÜÕ橵Ć╗ńÉåÕĆ╝ńÅŁÕ«żµ£ēĶĄĄĶīéõĖ░ńŁēõĖēõĮŹÕÉīÕ┐ŚÕÅéÕŖĀÕ╣ČõĮ£õ║å Ķ»”ń╗åĶ«░ÕĮĢŃĆé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Õ£©Ķ┐ÖµĀĘńÜäõ╝ÜõĖŖõĖŹĶ«▓õ┐ØÕ橵ü®µØźńÜäĶ»Ø’╝īÕ┐ģńäČń╗ÖķéŻõ║øÕÅŹÕ橵ü®µØźńÜä µĆصĮ«ĶĄĘÕł░õĖĆń¦ŹµÜŚńż║õĮ£ńö©ŃĆé
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┤┤Õć║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ńÜäÕż¦ÕŁŚÕÉÄÕćĀÕż®ķćī’╝īµ▒¤ķØÆõĖĆõ╝ÖõĖĆńø┤µ▓Īµ£ēõĮ£Õć║ ÕÅŹÕ║öŃĆéÕż¦ń║” 8 µ£łõĖŁµŚ¼’╝īńö▒µłÜµ£¼ń”╣Õć║ķØóÕŽÕŖ×õ║ŗń╗äńÜäõĖōĶüīÕģܵĆ╗µö»õ╣”Ķ«░ńÄŗķüōµśÄń╗äń╗ćõ║║ Ķ░ā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āīµÖ»ÕÆīµ┤╗ÕŖ©µāģÕåĄŃĆéńÄŗķüōµśÄµīēµłÜµ£¼ń”╣ńÜäÕĖāńĮ«’╝īÕģłµēŠĶ«░ĶĆģń½ÖńÜä ÕćĀõĮŹĶ«░ĶĆģĶ┐øĶĪīĶ░āµ¤ź’╝īÕ£©Ķ░āµ¤źĶ┐ćń©ŗõĖŁ’╝īĶ«░ĶĆģń½Öµ£ēõĖ¬Õł½Ķ«░ĶĆģÕÅŹµśĀ’╝īĶ«░ĶĆģń½ÖĶ░āµ¤źń╗äõĖŁ µ£ēńÜäĶ«░ĶĆģÕÉ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Ü䵳ÉÕæśµ£ēńēĄĶ┐×’╝īĶ░āµ¤źń╗ōĶ«║ÕÅ»ĶāĮŌĆ£õĖŹÕ«óĶ¦éŌĆØŃĆéńÄŗķüōµśÄ ĶĆāĶÖæÕł░Ķ┐Öń¦ŹµäÅĶ¦ü’╝īõĮåÕ╣ȵ▓Īµ£ēõĖŁµŁóĶ«░ĶĆģń½ÖĶ░āµ¤źń╗äńÜäĶ░āµ¤ź’╝īÕŬµś»ÕÅłķ揵¢░ń╗äń╗ćõ║åÕŖ×õ┐Ī ń╗äńÜäÕćĀõĖ¬õ║║’╝īÕÅ”µÉ×õĖƵæŖÕÉīµŚČĶ┐øĶĪīĶ░āµ¤źŃĆéń╗ÅĶ┐ćÕćĀÕż®ńÜäĶ░āµ¤ź’╝īµÉ£ķøåõ║åõĖĆõ║øµØɵ¢Ö’╝īõĖż õĖ¬Ķ░āµ¤źń╗äĶ”üµ▒éÕÉæńÄŗķüōµśÄµ▒ćµŖźĶ░āµ¤źÕłØµŁźń╗ōµ×£ÕÆīÕ£©Ķ░āµ¤źĶ┐ćń©ŗõĖŁķüćÕł░ńÜäķŚ«ķóśŃĆé
Ķ░ā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ص£¼µØźµś»ńÄŗķüōµśÄõ║▓Ķ欵ŖōńÜä’╝īµłæõĖĆńø┤µ▓Īµ£ēÕÅéõĖÄ’╝īĶĆīńÄŗķüōµśÄ Õ£©ÕÄ╗Ķ«░ĶĆģń½ÖÕɼõĖżõĖ¬Ķ░āµ¤źń╗äµ▒ćµŖźÕēŹ’╝īõĖĆÕåŹĶ«®µłæÕÉīõ╗¢õĖĆĶĄĘÕÄ╗Õɼµ▒ćµŖź’╝īÕĖ«õ╗¢Õć║Õć║õĖ╗µäÅ ’╝īµłæÕÅ¬ÕźĮõ╗ÄÕæĮŃĆéµ▒ćµŖźõ╝ܵś»Õ£©ĶŖ▒ÕøŁµØæõĖĆÕÅĘĶ«░ĶĆģń½ÖÕ╝ĆńÜä’╝īÕÅéÕŖĀµ▒ćµŖźõ╝ÜńÜäõĖ╗Ķ”üµś»Ķ░āµ¤ź ń╗äńÜäÕÉīÕ┐Ś’╝īĶ«░ĶĆģń½ÖĶ┤¤Ķ┤Żõ║║ÕŠÉÕŁ”Õó×õ╣¤õĖĆĶĄĘÕɼõ║åµ▒ćµŖźŃĆ鵏«µłæÕø×Õ┐å’╝īµ▒ćµŖźõĖ╗Ķ”üĶ░łõ║åõ╗ź õĖŗÕåģÕ«╣ŃĆé
õĖĆŃĆüµēĆĶ░ō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صś»ÕīŚõ║¼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ńÜäõĖĆõĖ¬Õ░ÅńŠżõ╝Śń╗äń╗ć’╝īÕÅéõĖ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µ┤╗ÕŖ©ńÜäõ║║ÕŠłÕ░æŃĆéõ╗¢õ╗¼ÕÅĘń¦░ŌĆ£ÕģĄÕøóŌĆØÕĖ”µ£ēĶÖÜÕ╝ĀÕŻ░ÕŖ┐’╝īń╗ÖĶć¬ÕĘ▒ÕŻ«Ķāå’╝īĶŠŠÕł░Ķ┐ʵāæ ńŠżõ╝ŚńÜäńø«ńÜäŃĆéÕģČÕ«×ÕÅéÕŖĀµö╗Õć╗Õ橵ü®µØźµ┤╗ÕŖ©ńÜäõ║║µĢ░Ķ┐×õĖĆõĖ¬µÄÆõ╣¤µ▓Īµ£ē’╝īÕ£░Õ£░ķüōķüōńÜäŌĆ£ õĖĆÕ░ŵƫŌĆØŃĆé
õ║īŃĆüµ£ēńÜäõ║║µĆĆń¢æõĖŁÕż«µ¢ćķØ®Ķ«░ĶĆģń½Öµ£ĆµŚ®ÕÉæ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ÕÅŹµśĀ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 ÕÅŹµĆ╗ńÉåµ┤╗ÕŖ©ńÜäķĆÜĶ«»Õæś’╝īĶāĮÕż¤ķéŻõ╣łÕćåńĪ«ÕÅŖµŚČÕ£░µÄīµÅ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ÜäÕŖ©ÕÉæ’╝īĶé»Õ«Ü ÕÉ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ķ¬©Õ╣▓ÕłåÕŁÉµ£ēÕ»åÕłćĶüöń│╗’╝īÕÉ”ÕłÖÕŠłķÜŠõ║åĶ¦ŻÕł░Ķ┐Öń¦ŹµĀĖÕ┐āµ£║Õ»åŃĆé
’╝łµØźĶć¬ŃĆŖĶ¬░µś»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ńÜäÕÉÄÕÅ░ŃĆŗ’╝ē
µīē:µ¢ćķØ®õĖŁµēĆĶ░ō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ŌĆØĶ┐ÖõĖĆńźĖÕÅŖÕŹāõĖćõ║║ńÜäÕż¦ÕåżµĪł’╝īÕŹüÕłå ÕģĖÕ×ŗÕ£░ĶĪ©ńÄ░Õć║µ»øµ│ĮõĖ£ÕÅŖÕģČŌĆ£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ŌĆØńÜ䵌Āµ│ĢµŚĀÕż®ÕÆīĶŹēĶÅģõ║║ÕæĮŃĆéõ╗ģõ╗ģÕģČõĖŁ õĖĆõĖ¬Ķ░ü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ÕÉÄÕÅ░ŌĆØńÜäķŚ«ķóś’╝īõ╗¢õ╗¼Õ░▒ÕÅ»õ╗źõ╗ŖÕż®Ķ┐ÖµĀĘĶ»┤’╝īµśÄÕż®ķ鯵ĀĘĶ«▓’╝īń┐╗õ║æĶ”å ķø©’╝īķÜŵäŵ×äķÖĘŃĆé
Õ橵ü®µØź 1969 Õ╣┤ 6 µ£ł 28 µŚźµÄźĶ¦üõĖŁÕøĮń¦æÕŁ”ķÖóÕō▓ÕŁ”ńżŠõ╝Üń¦æÕŁ”ķā©Õ«Żõ╝Āķś¤ÕÆīÕż¦ĶüöÕ¦öµŚČ ńÜäĶ«▓Ķ»ØõĖŁĶ»┤:
զܵ¢ćÕģā 9 µ£łõ╗ĮÕÅæĶĪ©µ¢ćń½Āńé╣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صś»ÕÅŹÕŖ©ń╗äń╗ć’╝īõĖ╗ÕĖŁ 8 µ£łõ╗ĮÕ░▒µŖōõĮÅõ║å’╝īõĖ╗ÕĖŁ ń£ŗńÜäÕćå......õĖ╗ÕĖŁÕŠłÕ┐½Õ░▒ÕÅæńÄ░õ║å’╝īń¤øÕż┤õĖŹÕ»╣ŃĆéÕĤµØźÕÉÄÕÅ░Õ░▒µś»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ŃĆéĶĄĘÕż┤’╝ī µłæõ╗¼µā│ÕłåÕī¢õ╗¢õ╗¼’╝īµŖŖµłÜµ£¼ń”╣ÕłåÕć║µØź’╝īÕ«×ķÖģõĖŖõ╗¢õ╗¼µś»õĖĆõ╝ÖŃĆé
(Õ橵ü®µØźÕ»╣õĖŁÕøĮń¦æÕŁ”ķÖó Õō▓ÕŁ”ńżŠõ╝Üń¦æÕŁ”ķā©õĖżµ¼ĪĶ░łĶ»ØõĖŁµ£ēÕģ│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ÕåģÕ«╣ŃĆé1969.06.28)
µ▒¤ķØÆ 1969 Õ╣┤ 8 µ£ł 14 µŚźµÄźĶ¦üµ¢ćĶē║ÕÅŻÕÉīÕ┐ŚĶ░łĶ»ØõĖŁĶ»┤: 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صś»õĖ¬ÕÅŹķØ®ÕæĮń╗äń╗ćŃĆéõ╗¢õ╗¼ńÜäÕÉÄÕÅ░µØ©ŃĆüõĮÖŃĆüÕéģ’╝īĶ┐śµ£ēµĘĘĶ┐ø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ÜäÕØÅ
õ║║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ŃĆéĶ┐ÖÕģŁõĖ¬õ║║õĖƵ¢╣ķØóµēōńØĆõ║║µ░æĶ¦ŻµöŠÕåøńÜ䵌ŚÕÅĘ;ÕÅ”õĖƵ¢╣ķØóµēōńØĆõĖŁÕż«µ¢ć ķØ®ńÜäµŗøńēī’╝īµÉ×ÕĮóŌĆ£ÕĘ”ŌĆØÕ«×ÕÅ│......
1970 Õ╣┤ 3 µ£ł 27 µŚźŃĆŖ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ģ│õ║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ńÜäķĆÜń¤źŃĆŗ
57’╝łõĖŁÕÅæ[1970]20 ÕÅĘ)õĖŁń¦░: 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’╝īÕ£©ÕÅŹķØ®ÕæĮõĖżķØóµ┤ŠĶé¢ÕŹÄŃĆüµØ©µłÉµŁ”ŃĆüõĮÖń½ŗķćæŃĆüÕéģÕ┤ćńó¦
ŃĆüńÄŗÕŖøŃĆüÕģ│ķöŗŃĆüµłÜµ£¼ń”╣µōŹń║ĄõĖŗ’╝īÕÉæ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ńī¢ńŗéĶ┐øµö╗’╝īńĮ¬Õż¦µüȵ×üŃĆé
ŃĆŖÕ橵ü®µØźÕģ│õ║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ÕćĀµ¼ĪĶ░łĶ»ØŃĆöµæśÕĮĢŃĆĢŃĆŗõĖŁ’╝ī1970 Õ╣┤ 11 µ£ł 4 µŚźńÜä Ķ«▓Ķ»ØķćīĶ»┤:
1968 Õ╣┤õĖĆõ║īµ£łõ╗ĮÕÅæńÄ░õ║å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µś»ŌĆ£516ŌĆØÕÉÄÕÅ░õĖŹõ╣ģ’╝īÕÅłÕÅæńÄ░µØ©ŃĆüõĮÖŃĆüÕéģŃĆé
Õ橵ü®µØźŃĆŖÕ£©ÕŹÄÕīŚõ╝ÜĶ««õĖŖńÜäĶ«▓Ķ»Ø¶Å░Ćń║▓ŃĆŗ(õĖĆõ╣ØõĖāõĖĆÕ╣┤õĖƵ£łõ║īÕŹüÕøøµŚź)õĖŁµē╣ÕłżķÖł õ╝»ĶŠŠĶ»┤:
õ╗¢Õ£©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ÉŹõĖ║ń╗äķĢ┐’╝īÕ«×ÕłÖÕÅŹÕ»╣õĖŁÕż«µ¢ćķØ®’╝īĶāīńØĆõĖŁÕż«µ¢ćķØ®µÉ×ÕØÅõ║ŗŃĆé...... õ╗¢µś»Ķé¢ÕŹÄŃĆüµØ©ŃĆüõĮÖŃĆüÕéģŃĆü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ŃĆü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ńÜäķ╗æÕÉÄÕÅ░’╝īµś» ÕÅŹÕģÜõ╣▒ÕåøńÜäńĮ¬ķŁüńźĖķ”¢ŃĆé
(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ĶĮ¼ÕÅæŌĆ£ÕÅŹÕģÜÕłåÕŁÉķÖłõ╝»ĶŠŠńÜäńĮ¬ĶĪīµØɵ¢ÖŌĆضÅ░üµ”éĶ”ü¶Å░é’╝ī 1971.01.26)
1971 Õ╣┤ 6 µ£ł 30 µŚźõĖŁÕż«õĖōµĪłÕ░Åń╗äĶüöÕÉłÕŖ×Õģ¼Õ«żķÖłõ╝¤Õ£©Õģ│õ║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┐ÉÕŖ© ńÜäĶ«▓Ķ»ØõĖŁĶ»┤:
õ╗ÄõĖĆõ║øÕŹĢõĮŹńÜäµāģÕåĄń£ŗ’╝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ĖŖÕ▒鵳ÉÕæśµāģÕåĄÕżÜµś»ÕÅøÕŠÆŃĆüńē╣ÕŖĪŃĆüÕÅŹķØ®ÕæĮõĖż ķØóµ┤Š’╝īµś»ÕłśÕ░æÕźćĶĄä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ńÜäķ╗æńÅŁÕ║ĢŃĆéõ╗¢õ╗¼ńÜäÕŗŠń╗ōńö▒µØźÕĘ▓õ╣ģŃĆé
õĖŁÕż«õĖōµĪłń╗äŃĆŖÕģ│õ║ÄÕøĮµ░æÕģÜÕÅŹÕģ▒ÕłåÕŁÉŃĆüµēśµ┤ŠŃĆüÕÅøÕŠÆŃĆüńē╣ÕŖĪŃĆüõ┐«µŁŻõĖ╗õ╣ēÕłåÕŁÉķÖłõ╝» ĶŠŠńÜäÕÅŹķØ®ÕæĮÕÄåÕÅ▓ńĮ¬ĶĪīńÜäÕ«Īµ¤źµŖźÕæŖŃĆŗ(1972.07.01)õĖŁĶ»┤:
µ×ŚÕĮ¬ŃĆüķÖłõ╝»ĶŠŠµś»ÕÅŹÕģÜõ╣▒Õåø’╝īµīæÕŖ©µŁ”µ¢ŚńÜäńĮ¬ķŁüńźĖķ”¢’╝ī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 ķøåÕøóńÜäķ╗æÕÉÄÕÅ░’╝īµś»ÕøĮÕåģĶó½µēōÕĆÆńÜäÕ£░õĖ╗ĶĄäõ║¦ķśČń║¦ÕÆīÕĖØŃĆüõ┐«ŃĆüÕÅŹÕ£©µłæõ╗¼ÕģÜÕåģńÜäõ╗ŻńÉå õ║║’╝īĶ«ĖÕżÜķ¼╝õ║ŗµāģńÜäµĀ╣ÕŁÉÕ░▒Õ£©Ķ┐ÖķćīŃĆé(ŃĆŖ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ģ│õ║ĵē╣ÕÅæŃĆłÕģ│õ║ÄÕøĮµ░æÕģÜÕÅŹÕģ▒ÕłåÕŁÉŃĆüµēśµ┤ŠŃĆüÕÅøÕŠÆŃĆüńē╣ÕŖĪŃĆüõ┐«µŁŻõĖ╗õ╣ēÕłåÕŁÉķÖłõ╝»ĶŠŠńÜäÕÅŹķØ®ÕæĮÕÄåÕÅ▓ńĮ¬ĶĪīńÜäÕ«Īµ¤źµŖźÕæŖŃĆēńÜäķĆÜ ń¤źÕÅŖķÖäõ╗ȵØɵ¢ÖŃĆŗ’╝ī1972.07.02;õĖŁÕÅæ[1972]25 ÕÅĘ)
ŃĆŖ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ń║¬ÕŠŗµŻĆµ¤źÕ¦öÕæśõ╝ÜÕģ│õ║ÄĶ░óÕ»īµ▓╗ķŚ«ķóśńÜäÕ«Īµ¤źµŖźÕæŖŃĆŗ(õĖĆõ╣ØÕģ½ŌŚŗÕ╣┤õ╣ص£ł õ║īµŚź)õĖŁĶ»┤:
Õ£©Ķ┐Įµ¤źµēĆĶ░ō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ÉÄÕÅ░µŚČ’╝īĶ░óÕ»īµ▓╗Õ«Żń¦░’╝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ķ╗æÕÉÄÕÅ░ŌĆ£µś»ÕłśŃĆüķéōńĢÖ õĖŗµØźńÜä’╝īÕåøķś¤Õ░▒µś»µØ©(µłÉµŁ”)ŃĆüĶé¢(ÕŹÄ)ŃĆüĶ┐śµ£ēÕÅČ(ÕēæĶŗ▒)ŃĆüÕŠÉ(ÕÉæÕēŹ)ŌĆØŃĆéõĖĆ õ╣ØÕģŁÕģ½Õ╣┤õ║īµ£ł’╝īĶĄĄńÖ╗ń©ŗÕÆ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ĖōµĪłń╗äķĢ┐ķÖłõ╝¤’╝īµīēńģ¦Ķ░óÕ»īµ▓╗ńÜäĶ┐ÖõĖƵijµäÅ’╝īÕ£© ń╗śÕłČńÜäŃĆŖÕÅŹķØ®ÕæĮń╗äń╗ćŌĆ£ķ”¢ķāĮõ║ö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╗äń╗ćń│╗ń╗¤ÕøŠŃĆŗÕÉÄÕÅ░µĀÅķćī’╝īÕĪ½ÕåÖõĖŖõ║åŌĆ£ÕÅČŃĆüÕŠÉ ŃĆüµØ©ŃĆüĶé¢ŌĆØŃĆé(ŃĆŖ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µē╣ĶĮ¼õĖŁÕż«ń║¬ÕŠŗµŻĆµ¤źÕ¦öÕæśõ╝ÜÕģ│õ║ÄÕ║Ęńö¤ŃĆüĶ░óÕ»īµ▓╗ķŚ«ķóśńÜäõĖżõĖ¬ Õ«Īµ¤źµŖźÕæŖŃĆŗ’╝ī1980.10.16)
µ║Éõ║Ä’╝Ü’╝ł’Į×Õ«ŗµ░Ėµ»ģõĖ╗ń╝¢ŃĆŖõĖŁÕøĮ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µ¢ćÕ║ōŃĆŗ
’Į×ŃĆŖĶ░ü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ÉÄÕÅ░ŃĆŗõĮ£ĶĆģ’╝ÜńÄŗÕ╣┐Õ«ć’╝ē
µīē:õĮ£õĖ║µ¢ćķØ®õĖŁõĖĆõĖ¬µ£Ćń¢»ńŗéńÜäµĢ┤õ║║Ķ┐ÉÕŖ©’╝ī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╣ŗµēĆõ╗źõ╝ܵēōÕć╗ŃĆüõ╝ż Õ«│ķéŻõ╣łÕżÜõ║║’╝īÕģČõĖŁõĖĆõĖ¬ķćŹĶ”üÕĤÕøĀ’╝īÕ░▒µś»Õ橵ü®µØźµÅÉÕć║ńÜäŌĆ£ķćŹńĮ¬ĶĪīŌĆØĶĆīõĖŹķćŹÕĮóÕ╝Å(µś»ÕÉ” ÕĪ½ĶĪ©ÕÅéÕŖĀń╗äń╗ć)ńÜäµĖģµ¤źµ¢╣ķÆłŃĆéõ╗¢Õ£©Ķ┐Öń»ćĶ«▓Ķ»ØõĖŁÕ░▒µśÄńĪ«µÅÉÕć║:ŌĆ£µś»õĖŹµś»ÕÅéÕŖĀń╗äń╗ć’╝ī ÕĪ½ĶĪ©µ▓Īµ£ē’╝īõĖŹµś»õĖ╗Ķ”üńÜäŃĆéĶ”üķ揵£¼Ķ┤©’╝īńĮ¬ĶĪīÕ░▒µś»µ£¼Ķ┤©’╝īÕĮóÕ╝ŵś»ń¼¼õ║īõĮŹńÜäŃĆéŌĆØĶ┐ÖõĖƵ¢╣ ķÆłńÜäµÅÉÕć║’╝īõĖ║µĖģµ¤źĶĆģµ╗źµēōµŚĀĶŠ£Õż¦Õ╝Ćõ║åµ¢╣õŠ┐õ╣ŗķŚ©ŃĆé
Õ橵ü®µØźµÄźĶ¦üÕż¢õ║ŗÕÅŻµĀĖÕ┐āń╗äÕåøÕ«Żķś¤ÕĘźÕ«Żķś¤Ķ┤¤Ķ┤Żõ║║µŚČ Õģ│õ║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µīćńż║
Õ橵ü®µØźĶ░łĶ»Ø
1970.11.01
ŃĆ¢Õ橵ü®µØźµĆ╗ńÉå 11 µ£ł 1 µŚźŃĆü9 µŚźŃĆü18 µŚźŃĆü20 µŚźÕøøµ¼ĪµÄźĶ¦üÕż¢õ║ŗÕÅŻµĀĖÕ┐āń╗äŃĆüÕåøÕ«Żķś¤ŃĆü
ÕĘźÕ«Żķś¤Ķ┤¤Ķ┤Żõ║║’╝īĶ░łĶ»ØõĖŁÕģ│õ║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ķā©ÕłåµæśĶ”üŃĆŚ
õĖĆŃĆüÕ»╣ 1970 Õ╣┤ŌĆ£õĖēõ║īõĖāŌĆØķĆÜń¤źńÜäķśÉĶ┐░ ŌĆ£õ╣ØÕż¦ŌĆØõ╗źÕÉÄ’╝īµ¢ćĶē║ÕŹĢõĮŹ¶Å░ĆÕć║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Ćé1 µ£ł 24 µŚźµłæõ╗¼µēŹĶ«▓ńÜä’╝īÕģČ
õ╗¢ÕŹĢõĮŹõ╗źÕēŹõĖŹń¤źķüōŃĆéõĖŁÕż« 3 µ£ł 27 µŚźÕÅæõ║åõĖ¬µØɵ¢Ö’╝īĶ«▓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 ’╝īÕ£©ÕÅŹķØ®ÕæĮõĖżķØóµ┤ŠĶÉ¦ÕŹÄŃĆüµØ©ŃĆüõĮÖŃĆüÕéģŃĆü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µōŹń║ĄõĖŗ’╝īÕÉæ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µ¢ćÕī¢Õż¦ ķØ®ÕæĮńī¢ńŗéĶ┐øµö╗’╝īńĮ¬Õż¦µüȵ×üŃĆéµ£ēõ║øõ║║Ķ«żõĖ║µĀ╣µ£¼õĖŹÕŁśÕ£©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øåÕøó’╝īÕ»╣ 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ص×üõĖ║µŖĄĶ¦”’╝īńöÜĶć│õĖ║õ╗¢õ╗¼ń┐╗µĪł’╝īµś»Õ«īÕģ©ķöÖĶ»»ńÜäŃĆéÕÉÄķØóĶ»┤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 õĖĆÕģŁŌĆص¢Śõ║ēÕĘ▓ń╗ÅÕ▒ĢÕ╝Ć’╝īÕģČÕ«×õ╣¤µ▓Īµ£ēÕż¦Õ▒ĢÕ╝Ć’╝īµ▓ĪĶ»┤µĖģµźÜ’╝īµ£ēõ║øÕŹĢõĮ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Šł ķÜÉĶöĮ’╝īõĖƵÉ×µĘ▒õ║å’╝īµāģÕåĄÕ░▒õĖŹµśÄŃĆéµ£ēńÜäÕŹĢõĮŹÕć║ńÄ░õ║åµē®Õż¦Õī¢’╝īÕÉÄķØóÕćĀµ«ĄõĖ╗Õ»╝µĆصā│µś» ķś▓µŁóµē®Õż¦Õī¢ŃĆé
µ¢ćõ╗ČÕģ▒Õøøµ«Ą’╝īÕēŹõĖƵ«ĄõĖŹĶ”üĶ»┤µ▓Īµ£ē’╝īÕÉÄÕćĀµ«ĄµĆصā│µś»ķś▓µŁóµē®Õż¦Õī¢’╝īµ▓Īµ£ēĶ«▓ńĮ¬ńŖČ ÕÆīµÅŁķ£▓ÕÉĵĆÄõ╣łµÉ×µ│Ģ’╝īõĖōµĪłÕĘźõĮ£ń╗äÕåģµ¤źÕż¢Ķ░āńøĖń╗ōÕÉł’╝īÕĮōµŚČµś»ķ£ĆĶ”üńÜä’╝īµē®Õż¦Õī¢õĖ╗Ķ”ü Ķ«▓µ¢ćĶē║ÕŹĢõĮŹÕÆīÕŁ”ķā©’╝īõĖĆõĖ¬µ¢ćõ╗ČÕŬĶāĮĶ«▓õĖ¬õĖ╗Õ»╝µ¢╣ķØó’╝īµÉ×ÕŠŚÕŠłÕģ©ķØóõĖŹÕÅ»ĶāĮŃĆé
õ║īŃĆüÕģ│õ║Ä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µĆ¦Ķ┤©ķŚ«ķóś 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’╝īĶ┐ÖõĖ¬ķøåÕøóÕ«ÜµĆ¦µś»õ╝¤Õż¦ķóåĶó¢µ»øõĖ╗ÕĖŁĶ»┤ńÜä’╝īķćŹńé╣
µś»ÕÅŹķØ®ÕæĮŃĆéõ╗¢õ╗¼µÉ×ķś┤Ķ░ŗ’╝īÕÅŹÕ»╣µ»øõĖ╗ÕĖŁ’╝īÕÅŹÕ»╣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’╝īÕÅŹÕ»╣µ»øµ│ĮõĖ£ µĆصā│’╝īõ╗¢õ╗¼õĖōķŚ©µÉ×Õ░ÅķüōµČłµü»’╝īõĮĀĶ”üõ╗¢õĖŹµÉ×õ╗Ćõ╣ł’╝īõ╗¢Õ░▒ķØ×µÉ×ŃĆéõĖŹĶ”üõ╗¢ÕÄ╗Õ«ēĶÉźµēÄÕ»©
’╝īõĖŹĶ”üõ╗¢ÕÄ╗Õż║µØā’╝īõ╗¢ķØ×Ķ”üÕÄ╗ŃĆéÕŬĶ”üµ¢ćķØ®(µ│©:µīćõĖŁÕż«µ¢ćķØ®Õ░Åń╗ä)ķćīµ£ēõĖĆõĖ¬õ║║Õć║µØź
Ķ»┤’╝īµł¢ĶĆģµś»õ╗¢õ╗¼õĖŗķØóńÜäõĖĆõ║øõ║║µ×ŚµØ░ŃĆüµ×ŚĶü┐µŚČŃĆüÕ橵ֻĶŖ│õĖĆĶ»┤Õ░▒ńøĖõ┐ĪŃĆ鵳æõ╗¼µÉ×µŁŻµŁŻ ÕĮōÕĮōÕģēµśÄńŻŖĶÉĮńÜä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Õ«×ĶĘĄ’╝īõ╗¢õ╗¼ÕÄ╗µÉ×ķś┤Ķ░ŗµ┤╗ÕŖ©’╝īµÉ×ķś┤Ķ░ŗµ┤╗ÕŖ©Õ░▒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 ÕģŁŌĆØ’╝īĶĆīõĖŹÕ£©ÕģČÕÉŹń¦░µś»õ╗Ćõ╣łŃĆéĶ┐Öõ║øõ║ŗõĖŹµś»õĖĆõĖ¬õ║║ÕüÜńÜä’╝īµś»õĖ¬ķøåÕøó’╝īķćŹńé╣õĖŹÕ£©Ķ┐Ö õĖ¬ń╗äń╗浜»ÕɔՎ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Ćé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┐ÖõĖ¬ÕÉŹń¦░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ĆÜń¤źÕÅæĶĪ©ÕÉÄ’╝īõ╗¢ õ╗¼ÕƤÕÅŻ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ĆÜń¤źõĖĆÕ╣┤õ╗źÕÉÄÕÅæĶĪ©µ£ēµäÅõ╣ē’╝īĶ”üµī¢Õć║ĶĄ½ķ▓üµÖōÕż½Õ╝Åõ║║ńē®’╝īÕł®ńö©Ķ┐ÖõĖ¬ÕÉŹń¦░’╝īńģĮÕŖ©µÉ×ķś┤Ķ░ŗµ┤╗ÕŖ©ŃĆéµēĆõ╗źõĖŹõĖĆÕ«ÜķāĮÕŽ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ń╗äń╗ćŃĆéÕĪ½ĶĪ©õĖŹÕĪ½ĶĪ©ķāĮ õĖŹµś»õĖ╗Ķ”üńÜä’╝īõĖ╗Ķ”üµś»õ╗¢õ╗¼ńÜäÕÅŹķØ®ÕæĮµ┤╗ÕŖ©’╝īõ╗¢ń¤øÕż┤ķÆłÕ»╣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’╝īĶ”üķćŹÕ£© ńĮ¬ĶĪīŃĆéõĖ╗Ķ”üµś»µ¤źõ╗¢õ╗¼ÕÅŹÕ»╣µ»øõĖ╗ÕĖŁ’╝īÕÅŹÕ»╣µ»øµ│ĮõĖ£µĆصā│’╝īÕÅŹÕ»╣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ÅĖõ╗żķā©’╝īÕÅŹ Õ»╣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ńÜäńĮ¬ĶĪīŃĆé
õĖē’╝īÕģ│õ║ÄõĖōµĪłõĖÄńŠżõ╝ŚĶ┐ÉÕŖ©ńøĖń╗ōÕÉłńÜäķŚ«ķóś ÕŖ×µ│ĢĶ┐śµś»Ķ”üÕÅæÕŖ©ńŠżõ╝Ś’╝īµē┐Ķ«żõ║åńÜäµēĆõ╗źÕ«╣µśōń┐╗’╝īÕ░▒µś»ÕøĀõĖ║µ▓Īµ£ēńŠżõ╝Ś’╝īńŠżõ╝ŚõĖŹń¤źķüō’╝īķóåÕ»╝ÕÆīńŠżõ╝ŚńøĖń╗ōÕÉł’╝īĶ”üÕåģķā©µÅŁÕÅæµŻĆõĖŠÕÆīÕż¢ķā©Ķ░āµ¤źń╗ōÕÉłŃĆé
õĖōµĪłõĖÄńŠżõ╝ŚĶ┐ÉÕŖ©ńøĖń╗ōÕÉł’╝īµØɵ¢ÖĶ”üõ║żń╗ÖńŠżõ╝ŚĶ«©Ķ«║µē╣ÕłżŃĆé
ÕøøŃĆüĶ”üķ揵£¼Ķ┤©’╝īĶ”üµŖōńĮ¬ĶĪīńÜäķŚ«ķóś’╝īÕ»╣õĖĆõ║øķćŹÕż¦µĪłõ╗ČĶ”üµ¤źõĖ¬µ░┤ĶÉĮń¤│Õć║ µś»õĖŹµś»ÕÅéÕŖĀń╗äń╗ć’╝īÕĪ½ĶĪ©µ▓Īµ£ē’╝īõĖŹµś»õĖ╗Ķ”üńÜäŃĆéĶ”üķ揵£¼Ķ┤©’╝īńĮ¬ĶĪīÕ░▒µś»µ£¼Ķ┤©’╝īÕĮó Õ╝ŵś»ń¼¼õ║īõĮŹńÜäŃĆéÕĮōńäČõ╣¤Ķ”üÕ╝äµĖģµźÜŃĆéķ╗æõ╝ÜķāĮÕ╝ĆńÜäŃĆéÕ░▒ńŁēõ║Äń╗äń╗ćÕģ│ń│╗õ║åŃĆéÕĮŁÕŠĘµĆĆ’╝ī ķ╗äÕģŗĶ»ÜńÜäµ┤╗ÕŖ©Õ░▒µś»ÕÅŹÕģÜńÜä’╝īĶ┐śķ£ĆĶ”üµłÉń½ŗõ╗Ćõ╣łń╗äń╗ć?ń£¤µŁŻńÜäµĀĖÕ┐āõĖŹõĖĆÕ«ÜÕĪ½ĶĪ©ÕÅéÕŖĀ ń╗äń╗ć’╝īõ╗¢õ╗¼ĶāīńØĆõĖŁÕż«Õ╝Ćõ╝Üķøåõ╝ÜĶ┐Öń¦ŹĶĪīÕŖ©Õ░▒µś»ńĮ¬ĶĪī’╝īµ£ēķøåõ╝ÜÕ░▒µś»µ£ēĶ«ĪÕłÆńÜäĶĪīÕŖ©ŃĆé
ÕŬĶ”üńĮ¬ĶĪīńĪ«Õ«×’╝īµŖōõĮÅÕćĀõ╗Čõ║ŗÕ░▒ÕÅ»õ╗źŃĆé ÕŹ½ńö¤ÕÅŻń¬üńĀ┤õ║åŌĆ£3.10ŌĆØÕ░▒Ķ¦ŻÕå│õ║åÕż¦ķŚ«ķóś’╝īÕż¢õ║ŗÕÅŻµś»ÕżÜÕćĀõĖ¬:ńü½ńā¦Ķŗ▒õ╗ŻÕŖ×Õżä
’╝īŌĆ£8.11ŌĆØÕż¦õ╝Ü’╝īÕ«ēĶÉźµēÄÕ»©’╝īÕż¢õ║żķā©Õż║µØā’╝īÕ░üķā©ÕģÜÕ¦öŃĆüµö┐µ▓╗ķā©Õż║µØā’╝īĶ┐ÖÕćĀõ╗Čõ║ŗ ÕĘ▓ń╗ÅÕż¤õ║å’╝īÕćĀÕ╣┤µØźĶĄ░õ║åÕ╝»ĶĘ»’╝īµłæõ╗¼µ£ēĶ┤Żõ╗╗’╝īõ╗źÕēŹµ▓Īµ£ēĶ«▓ķĆÅ’╝īĶ┐Öµ¼ĪµŖŖÕ«āĶ«▓ķĆÅ’╝īõĖŖ
ķØóµ£ēõĖĆõĖ¬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µīćµīź’╝īõĖŗķØóõĖŹõĖĆÕ«ÜÕŽĶ┐ÖõĖ¬ń╗äń╗ćŃĆéÕÉ┤õ╝ĀÕÉ»(µ│©:µøŠõ╗╗õĖŁÕøĮń¦æÕŁ”ķÖó
Õō▓ÕŁ”ńżŠõ╝Üń¦æÕŁ”ķā©ŃĆŖÕō▓ÕŁ”ńĀöń®ČŃĆŗµØéÕ┐Śõ╗ŻńÉåõĖ╗ń╝¢’╝īÕŁ”ķā©µ¢ćķØ®Ķ┤¤Ķ┤Żõ║║)’╝īÕ£©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
µłÉń½ŗµŚČÕĘ▓ń╗ÅõĖŹÕ£©Ķ┐Öķćīõ║å’╝īõ╗¢ÕÅ»õ╗źĶ»┤ÕÆī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ص▓Īµ£ēÕģ│ń│╗’╝īÕłśķø©µØź(µ│©:ÕīŚõ║¼Õż¢
ÕøĮĶ»ŁÕŁ”ķÖóń║óÕŹ½ÕģĄ’╝īń║󵌌ķĆĀÕÅŹÕøóĶ┤¤Ķ┤Żõ║║)Ķ»┤õ╗¢µ»ö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┐ś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’╝īķéŻÕźĮÕ░▒
Õ«ÜÕśøŃĆéµŖŖń╗äń╗ćÕĪ½ĶĪ©ń£ŗÕŠŚÕż¬ķćŹõ║å’╝īµ£ēńÜäÕ£░µ¢╣µłÉń½ŗń╗äń╗ć’╝īµ£ēńÜäÕ£░µ¢╣Ķ┐śµ▓Īµ£ēµØźÕŠŚÕÅŖµłÉ ń½ŗ’╝īÕ░▒µś»õĖ║õ║åĶ”üÕŠŚõĖ¬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ĶĪ©µĀ╝’╝īń╗äń╗ćķŚ«ķóśÕ░▒õĖŹĶāĮիܵĪł’╝īĶ┐Öń£¤µś»ÕÅ»ń¼æńÜä ŃĆé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░▒µś»Õł®ńö©ŃĆŖ5.16 ķĆÜń¤źŃĆŗõĮ£ÕÅĘÕż’╝īµÉ×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µ┤╗ÕŖ©’╝īõ╗¢õ╗¼Õ£©õĖĆĶĄĘÕ╝Ć ķ╗æõ╝Ü’╝īµÉ×ń¦śÕ»åÕÅŹÕģܵ┤╗ÕŖ©’╝īÕ░▒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╗äń╗ćµ┤╗ÕŖ©ŃĆéÕ”éńü½ńā¦Ķŗ▒õ╗ŻÕŖ×Õżä’╝īÕå▓õĖŁ(Õż« )µ£║(Ķ”üÕ▒Ć)ķāĮµ£ēĶ░ü’╝īµĆÄõ╣łÕÄ╗ńÜä’╝īĶ”üĶ«▓µĖģµźÜ’╝īµģóµģóÕ£░Õż┤Õż┤Õ░▒µĖģµźÜõ║åŃĆéõ╗¢Ķ«żńĮ¬õ║åŃĆé
õĮĀõĖŹÕżäńÉå’╝īÕÄ╗Ķ┐Įń╗äń╗ć’╝īõĖŹÕ«ÜµĪł’╝īÕ░▒µś»Õ«ĮÕż¦µŚĀĶŠ╣’╝īÕÆīÕźĮõ║║õĖƵĀĘń£ŗÕŠģ’╝īÕ░▒µś»õĖĆķŻÄÕÉ╣ ŃĆé
õ║öŃĆüĶ”üµ£ēÕćåÕżćŃĆüõĖŹµēōµŚĀÕćåÕżćõ╣ŗõ╗Ś’╝īĶ”üµŖŖµØɵ¢ÖÕćåÕżćÕźĮ µĆ╗Ķ”üµ£ēõ║øµØɵ¢ÖµēŹµ£ēµäŵĆØŃĆéÕģēµ£ēķéŻõ║øµŖĮĶ▒ĪńÜä’╝īõĖĆĶł¼ńÜäõĖŹĶĪī’╝īĶ”üµ£ēń½ÖÕŠŚõĮÅĶäÜńÜä
µØɵ¢Ö’╝īÕģ¼Ķ»Ėõ║Äõ╝Ś’╝īµēŹĶāĮÕÅæÕŖ©ńŠżõ╝ŚŃĆé
µīē:ÕĮōÕ╣┤ńÜä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┐ÉÕŖ©’╝īµĖģµØźµĖģÕÄ╗Õł░Õ║Ģõ╗Ćõ╣ł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¦ŗń╗łµ▓Īõ║║Ķ»┤µĖģ µźÜŃĆéõĮåµś»õ║║õ╗¼ķĆɵĖÉÕÅæńÄ░Ķ┐ÖõĖ¬µĖģµ¤źńÜäń¤øÕż┤µś»Õ»╣ÕćåķĆĀÕÅŹµ┤ŠńÜäŃĆéÕÉäÕ£░ķüŁÕł░µĖģµ¤źńÜäÕ»╣Ķ▒Ī õĖ╗Ķ”üÕ░▒µś»µ¢ćķØ®ÕēŹµ£¤ńÜäķĆĀÕÅŹµ┤Š’╝īńē╣Õł½µś»ÕģČõĖŁµ»öĶŠāµ┐ĆĶ┐øńÜäõĖƵ┤ŠŃĆéĶ»╗Ķ┐Öń»ćõĖŁÕż«õĖōµĪłń╗ä ĶüöÕÉłÕŖ×Õģ¼Õ«żµ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Ķ┤¤Ķ┤Żõ║║ķÖłõ╝¤ńÜäĶ«▓Ķ»Ø’╝īÕ░▒ÕÅ»õ╗źµśÄńÖĮ’╝īÕĤµØźõ╗¢õ╗¼µēōÕć╗ńÜäÕ»╣Ķ▒Ī Õ░▒µś»ķĆĀÕÅŹµ┤Š’╝īĶ«▓Ķ»ØõĖŁÕłŚõĖŠńÜäµēĆĶ░ō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ŌĆ£ķś┤Ķ░ŗõĖÄńĮ¬ĶĪīŌĆØ’╝īÕ«×ķÖģõĖŖÕģ©ķāĮµś»ķĆĀÕÅŹµ┤Š Õż¦Õ╝ĀµŚŚķ╝ōńÜäÕģ¼Õ╝Ƶ┤╗ÕŖ©ŃĆéµ»øµ│ĮõĖ£õĖ║õ╗Ćõ╣łĶ”üÕ»╣Ķć¬ÕĘ▒ķ╝ōÕŖ©ŃĆüµēȵżŹĶĄĘµØźńÜäķĆĀÕÅŹµ┤ŠõĖŗµŁżńŗĀ µēŗ?Ķ┐Öµś»õĖ¬ķ£ĆĶ”üÕÅ”Õż¢ńĀöń®ČńÜäĶ»ŠķóśŃĆé
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ńÜäķś┤Ķ░ŗŃĆüńĮ¬ĶĪīÕÆīń╗äń╗ć(ĶŖéÕĮĢ)
µēĆĶ░ōµ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’╝īÕ«×ķÖģõĖŖÕ░▒µś»ķĢćÕÄŗķĆĀÕÅŹµ┤ŠŃĆéĶ┐ÖõĖĆńé╣µØ©Õ░ÅÕ滵Ś®Õ░▒ń£ŗķĆÅõ║åŃĆéÕ£©ÕĮōÕ▒ĆÕż¦Õ╝ĀµŚŚķ╝ōÕ£░Õ▒ĢÕ╝Ƶ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Ķ┐ÉÕŖ©ńÜ䵌ČÕĆÖ’╝īµØ©Õ░ÅÕ滵ŁŻµł┤ńØĆŌĆ£ÕÅŹķØ®ÕæĮŌĆØńÜäńĮ¬ÕÉŹÕ£©ńøæńŗ▒õĖŁµ£ŹÕłæŃĆéµØ©Õ░ÅÕć»ÕÆīķÜŠÕÅŗõ║żµĄüµĆصā│’╝īµīćÕć║’╝ܵ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Õ░▒µś»Ķ┐½Õ«│ķĆĀÕÅŹµ┤ŠŃĆé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Ķ┐ÉÕŖ©µś»ĶĆüµ»øõ╗ĵö»µīüķĆĀÕÅŹµ┤ŠÕł░Ķ┐½Õ«│ķĆĀÕÅŹµ┤ŠńÜäĶĮ¼ÕÅśŃĆéµØ©Õ░ÅÕć»Ķ«żõĖ║’╝īŌĆ£Ķ┐Öµ¼ĪĶ┐½Õ«│ķĆĀÕÅŹµ┤Š ’╝īĶĪ©ķØóõĖŖÕ橵ü®µØźÕŹüÕłåń¦»µ×ü’╝īõĮåÕÅæÕŖ©ĶĆģÕŹ┤µś»µ»øĶ»æõĖ£ŃĆéŌĆصةÕ░ÅÕć»Ķ┐śĶ»┤’╝ÜŌĆ£ŌĆśµ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Ķ┐ÉÕŖ©ŌĆÖĶ┐ÖõĖ¬ÕÉŹń¦░ÕÅ¢ÕŠŚÕźĮÕŠ«Õ”ÖŃĆé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ķĆÜń¤źŌĆÖµś»µ»øµ│ĮõĖ£ÕÅæÕŖ©µ¢ćķØ®ńÜäń¼¼õĖĆõĖ¬ķćŹĶ”üķĆÜń¤ź’╝īńÄ░Õ£©Ķ┐ÖõĖ¬Ķ┐ÉÕŖ©ÕÅŹ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’╝īĶ»┤µśÄµ»øµ│ĮõĖ£Ķ”üĶ┐½Õ«│õ╗¢Ķ┐ćÕÄ╗µö»µīüĶ┐ćńÜäõ║║ŃĆéµīēŌĆśõ║ö┬Ę õĖĆÕģŁŌĆÖńÜäńĮ¬ńŖČ’╝īµēƵ£ēķĆĀĶ┐ćÕÅŹńÜäõ║║ķāĮÕÅ»õ╗źń«Ś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’╝īõĮå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Õ«×ķÖģõĖŖµś»õĖ¬Õ╣ČõĖŹĶæŚÕÉŹńÜäÕćĀÕŹüõĖ¬õ║║ńÜäÕīŚõ║¼ÕŁ”ńö¤ń╗äń╗ć’╝īÕż¦ÕżÜµĢ░õ║║ķāĮõĖŹõ║åĶ¦Ż’╝īµēĆõ╗źÕĮōµØāµ┤ŠÕÅ»õ╗źµīēõ╗¢õ╗¼ńÜäÕ¢£ÕźĮõ╗╗µäÅÕ░åõ╗¢õ╗¼õĖŹÕ¢£µ¼óńÜäõ║║µīćń¦░õĖ║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’╝īÕŖĀõĖŖ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µś»ÕÅŹÕ橵ü®µØźńÜä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õ╣¤ÕÅ»õ╗źńö©ÕÅŹŌĆśõ║öõĖĆÕģŁŌĆÖµØźĶ«©ÕźĮÕ橵ü®µØźŃĆéŌĆØ
ķéŻõ╣ł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õĖ║õ╗Ćõ╣łĶ”üĶĮ¼Ķ┐ćÕż┤µØź’╝īõ╗ĵö»µīüķĆĀÕÅŹµ┤ŠÕÅśµłÉķĢćÕÄŗķĆĀÕÅŹµ┤ŠÕæó’╝¤µłæõ╗źõĖ║ÕģČÕĤÕøĀõ╣¤Õ╣ČõĖŹÕżŹµØéŃĆéÕøĀõĖ║ÕĮōÕłØµ»øµ│ĮõĖ£ÕÅæÕŖ©ńŠżõ╝ŚķĆĀÕÅŹ’╝īõ╗ģõ╗ģµś»õĖ║õ║åµēōÕĆÆÕłśÕ░æÕźćõĖĆõ╝Öµö┐µĢī’╝īÕ«×ĶĪīÕż¦µĖģµ┤Ś’╝īõĖƵŚ”Ķ┐ÖõĖ¬ńø«ńÜäĶŠŠÕł░õ║å’╝īõĮ£õĖ║ÕĘźÕģĘńÜäķĆĀÕÅŹµ┤ŠÕ░▒Õż▒ÕÄ╗Õł®ńö©õ╗ĘÕĆ╝õ║åŃĆéÕÅłńö▒õ║ÄĶ”üµĀæń½ŗÕÆīń╗┤µŖżµēĆĶ░ōµ¢░ńö¤ń║óĶē▓µö┐µØāńÜäµØāÕ©ü’╝īĶ”üķ揵¢░ńĪ«ń½ŗÕģÜńÜäķóåÕ»╝õĖŹÕÅ»õŠĄńŖ»ńÜäÕÄ¤ÕłÖ’╝īĶ┐ÖÕ░▒ķ£ĆĶ”üń║”µØ¤ÕÆīń”üµŁóń¦Źń¦ŹŌĆ£ńŖ»õĖŖõĮ£õ╣▒ŌĆØńÜäķĆĀÕÅŹĶĪīõĖ║’╝īÕÅ»µś»ńŠżõ╝ŚķĆĀÕÅŹµ£¼µØźµś»µ»øµ│ĮõĖ£Õż¦ÕŖøķ╝ōÕŖ©ńÜä’╝īµ»øõĖŹÕźĮÕģ¼ńäČńÜäÕć║Õ░öÕÅŹÕ░ö’╝īõ║ĵś»õ╗¢Õ░▒ÕƤÕŖ®õ║ÄõĖĆõĖ¬ĶĽķĪ╗µ£ēńÜäÕÅŻĶóŗńĮ¬’╝īÕ»╣ķĆĀÕÅŹµ┤ŠõĖźÕŖĀµēōÕć╗’╝īõ╗źÕäåµĢłÕ░żŃĆéÕÅ”Õż¢’╝īÕ£©ÕēŹķśČµ«ĄńÜäĶ┐ÉÕŖ©õĖŁ’╝īÕż¦Õż¦Õ░ÅÕ░ÅńÜäÕ╣▓ķā©ķāĮÕÅŚÕł░Õå▓Õć╗’╝īńÄ░Õ£©ĶÖĮńäČķ揵¢░µÄīµØāõ║å’╝īõĮåĶéÜÕŁÉķćīķāĮĶ┐śµ£ēÕŠłÕż¦ńÜäµĆ©µ░ö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Ķ”üÕ«ēµŖÜõ╗¢õ╗¼’╝īÕ░▒Ķ”üń╗Öõ╗¢õ╗¼õĖĆõĖ¬µ£║õ╝ÜÕć║µ░öŃĆéĶĆīĶ┐Öõ║øÕ╣▓ķā©Ķć¬ÕĘ▒µŚóńäČõĖŹµĢóńø┤µÄźÕ»╣µ»øĶĪ©ńż║õĖŹµ╗Ī’╝īÕøĀµŁżõ╣¤Õ░▒µŖŖµĆ©µ░öķāĮµÆÆÕ£©ńŠżõ╝ŚĶ║½õĖŖ’╝īÕƤ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õ╣ŗÕÉŹÕ»╣ķĆĀÕÅŹµ┤ŠÕÅŹµö╗ÕĆÆń«ŚŃĆé
õĖŁÕģ▒õĖŁÕż«Õ£©Õģ©ÕøĮĶīāÕø┤ÕåģÕ╝ĆÕ▒ĢµĖģµ¤ź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Ķ┐ÉÕŖ©’╝īń«Ćń¦░µĖģµ¤źõ║öõĖĆÕģŁ’╝īµĢ░õ╗źńÖŠõĖćĶ«ĪńÜäÕ╣▓ķā©ńŠżõ╝ŚķüŁÕł░Ķ┐½Õ«│ŃĆéµ£ēÕŁ”ĶĆģõ╝░Ķ«ĪÕÅŚÕł░µĖģµ¤źńÜäõ║║õ╗źÕŹāõĖćĶ«Ī’╝īµĢ┤µŁ╗õ║║õ╗ź10õĖćĶ«ĪŃĆé
Ķ┐ÖÕ£║µĖģµ¤źĶ┐ÉÕŖ©õĖĆńø┤µīüń╗ŁÕł░1974Õ╣┤µē╣µ×Śµē╣ÕŁöĶ┐ÉÕŖ©’╝īõ╣ŗÕÉÄõĖŹõ║åõ║åõ╣ŗŃĆéµĖģµ¤źĶ┐ÉÕŖ©õĖŹõ╗ģõĖźķ揵ē®Õż¦Õī¢’╝īĶĆīõĖöµ╝öÕÅśµłÉÕģ©ÕøĮµĆ¦ńÜäõĖżµ┤ŠńŠżõ╝Śń╗äń╗ćÕż¦µĘʵłśŃĆé
õŠŗÕ”é’╝ܵ▒¤ĶŗÅń£üńÜäŌĆ£µĖģµ¤ź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ķüŗÕŗĢ
Õ£©µ▒¤ĶŗÅń£üńÜäµĖģµ¤źõ║ö┬ĘõĖĆÕģŁĶ┐ÉÕŖ©õĖŁ’╝īń£üķخզöõ╝ÜõĖ╗õ╗╗Ķ«ĖõĖ¢ÕÅŗõĖ╗Õ╝ĀŌĆ£µĘ▒µī¢ŌĆØ’╝īÕƤµ£║µēōÕć╗Õ╝éÕĘ▒’╝īÕģČõĖ╗µö┐ńÜäµ▒¤ĶŗÅń£üķخզöõ╝Ü45ÕÉŹÕĖĖÕ¦öõĖŁ25õ║║Ķó½µēōµłÉ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łåÕŁÉŌĆØ’╝īÕ£©µīüń╗Ł3Õ╣┤ÕżÜńÜäµĖģµ¤źĶ┐ćń©ŗõĖŁ’╝īÕģ©ń£ü25õĖćÕżÜõ║║Ķó½µēōµłÉ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łåÕŁÉŌĆØ’╝īĶČģĶ┐ć2000õ║║µŁ╗õ║ĪŃĆé
µ▒¤ĶŗÅń£üÕ¦öõ╣”Ķ«░ÕÉ┤Õż¦Ķā£õ╗źÕŹŚõ║¼Õż¦ÕŁ”õĖ║ń¬üńĀ┤ÕÅŻ’╝īµ┤ŠÕć║ŌĆ£Ķ░āµ¤źń╗äŌĆØĶ┐øķ®╗µĖģµ¤źŃĆéÕŹŚõ║¼Õż¦ÕŁ”ÕģłÕÉÄĶó½ĶĽķĪ╗µ£ēÕ£░µēōµłÉŌĆś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ÖÕłåÕŁÉńÜäÕĖłńö¤ÕæśÕĘźĶŠŠ1560õ║║’╝īÕŹĀÕĮōµŚČÕĖłńö¤ÕæśÕĘźµĆ╗µĢ░’╝ł4950õ║║’╝ēńÜäĶ┐æõĖēÕłåõ╣ŗõĖĆŃĆéÕģČõĖŁĶó½Õģ│µŖ╝µē╣µ¢ŚńÜäµ£ē389õ║║’╝īĶó½ÕłżÕłæńÜä16õ║║’╝īĶó½Ķ┐½Õ«│Ķć┤µŁ╗ÕżÜĶŠŠ28õ║║ŃĆé
µ▒¤ĶŗÅń£üÕå£õĖÜÕ▒Ć64ÕÉŹŌĆ£ńĢÖÕ«łõ║║ÕæśŌĆØ’╝īµ£ē39õ║║µēōµłÉ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ŃĆéµēōµłÉ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ńÜäÕ▒ĆķóåÕ»╝ÕŹĀ60%’╝īÕżäÕ«żĶ┤¤Ķ┤Żõ║║ÕŹĀ62%’╝īÕģܵö»ķā©Õ¦öÕæśÕŹĀ80%’╝īÕģÜÕæśÕŹĀ64%’╝īÕģܵö»ķā©ÕćĀõ╣ĵłÉõ║å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صö»ķā©ŃĆ鵏«µ▒¤Ķśćń£üńøĖķŚ£µ¢ćõ╗ČĶ«░ĶĮĮ’╝ܵ▒¤ĶŗÅń£üÕå£õĖÜÕ▒Ƶ£ēõĖĆõĖ¬ÕÅŚÕÉ┤Õż¦Ķā£ÕĮ▒ÕōŹńÜäÕ▒ĆķóåÕ»╝’╝īĶć¬ń¦░õ╝ÜŌĆ£ńøĖķØóŌĆØ’╝īõ╗¢õĖŹµŚČµĘ▒ÕģźÕÉäõĖ¬ŌĆ£µĘ▒µī¢Õ░Åń╗äŌĆØ’╝īõ╗źĶć│ķźŁÕÄģŃĆüõ╝ÜĶ««Õ«ż’╝īõ╗źŌĆ£ńøĖŌĆØÕć║Õō¬õĖ¬õ║║µś»ŌĆ£õ║öõĖĆÕģŁŌĆØŌĆöŌĆöĶ«▓Ķ»ØÕżÜńÜä’╝īµś»ŌĆ£ĶŗźµŚĀÕģČõ║ŗŌĆØ’╝øĶ«▓Ķ»ØÕ░æńÜä’╝īµś»ŌĆ£µĢģõĮ£ķĢćķØÖŌĆØ’╝øÕÉāķźŁÕżÜńÜä’╝īµś»ŌĆ£ÕćåÕżćķĪĮµŖŚŌĆØ’╝øÕÉāķźŁÕ░æńÜä’╝īµś»ŌĆ£Õ┐āõĖŁµ£ēķ¼╝ŌĆØ’╝øµł┤õĖĆķĪȵ֫ķĆÜÕĖĮÕŁÉ’╝īµłÉõ║åŌĆ£Ķüöń╗£µÜŚÕÅĘŌĆØ’╝øÕō╝õĖĆÕÅźµĀʵØ┐µłÅ’╝īµś»õĖ║ÕÉīõ╝ÖŌĆ£µēōµ░öŌĆØ’╝īÕłČĶ«óŌĆ£µö╗Õ«łÕÉīńø¤ŌĆØ’╝øĶ┐øõ╝ÜÕ£║µŚČĶĄ░µģóõ║å’╝īµś»ŌĆ£ÕīģĶó▒µ▓ēķćŹŌĆØ’╝øĶĄ░Õ┐½õ║å’╝īÕłÖÕÅłµś»ŌĆ£ÕåģÕ┐āń®║ĶÖÜŌĆØ’╝øń£ŗµŖźń║Ė’╝īµś»ŌĆ£µĆصā│õĖŹķøåõĖŁŌĆØ’╝øÕŁ”õ╣Āµ»øõĖ╗ÕĖŁĶæŚõĮ£’╝īµś»ŌĆ£µēōńØĆń║󵌌ÕÅŹń║󵌌ŌĆ”ŌĆ”ÕÅŹµŁŻõĖŹń«ĪµĆĵĀĘ’╝īõĖĆõĖŠõĖĆÕŖ©ķāĮÕÅ»õ╗źµłÉõĖ║ÕłżÕ«ÜńÜäĶ»üµŹ«ŃĆé
’╝łķŁüń£üÕ▒▒Õ»©┬ĘÕø×ķĪ¦µŁĘÕÅ▓-µæśĶć¬ńøĖķŚ£Ķ│ćµ¢ÖŃĆüÕø×µåČŃĆüµ¢ćń½ĀµĢ┤ńÉåµ▒ćńĘ©’╝ē
µłæńé║õ╗Ćķ║╝Õ░ŹĶ½ŗµ¤ź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ÅŹķØ®ÕæĮķøåÕ£śķĆÖÕĀ┤ķüŗÕŗĢĶ╝āńé║ķŚ£µ│©’╝īÕĆŗõ║║Ķ¬Źńé║Õ«āÕĆæÕģČÕ»”µ£ēÕł®µ¢╝Ķ¦Żķ¢ŗµ¢ćķØ®ÕŹüÕż¦Ķ¼ÄÕ£śõ╣ŗõĖĆńÜäŃĆīÕ橵ü®õŠåÕ£©Ķź┐ĶŖ▒Õ╗│Ķó½ń┤ģĶĪøÕģĄńĄäń╣öÕ£ŹÕø░Õģ®Õż®Õģ®Õż£õ║ŗõ╗ČŃĆŹŃĆé
Õ橵ü®õŠåµ¢ćķخգ©Ķź┐ĶŖ▒Õ╗│Ķó½Õ£ŹÕø░’╝īõĖĆńø┤µś»ńÅŠÕ£©Õģ¼ķ¢ŗĶ│ćµ¢ÖõĖŁµ▓Ƶ£ēµÅÉÕÅŖ’╝īńĢČõ║ŗõ║║ÕÆīÕ«śµ¢╣ķāĮµ£ēµäÅĶ┐┤ķü┐µł¢ĶĆģĶ¬¬ķÜ▒ń××ķĆÖõ╗Čõ║ŗ’╝īõĖĆĶł¼ńÜäõ║║ÕĘ▓ńČōõĖŹń¤źķüōõĖŹĶ¬Źńé║µøŠńČōńÖ╝ńö¤ķüÄķĆÖµ©ŻńÜäõ║ŗŃĆé
µōÜń©▒’╝īµ¢ćķØ®ÕłØµ£¤ń┤ģĶĪøÕģĄńĄäń╣öÕ£©Ķź┐ĶŖ▒ĶüĮÕ£Źµö╗Õ橵ü®õŠå’╝īÕÉŹńŠ®õĖŖµś»Ķ«ōÕ橵ü®õŠåĶ¬¬µĖģµŁĘÕÅ▓’╝īĶĪ©µśÄĶć¬ÕĘ▒ńÜäµģŗÕ║”µö»µīüĶ¬░’╝īÕ£©Ķ¦Ćķ╗×ŃĆüńŠżń£ŠńĄäń╣öõĖŖķĆ▓ĶĪīĶŠ©Ķ½¢’╝īĶ╝¬µĄüõĖŖķÖŻõĖŹĶ«ōÕ橵ü®õŠåõ╝æµü»’╝īµ▓Æõ║║Õć║ķØó’╝īõĖŖÕ▒żµ£ēµäÅĶ«ōÕæ©ÕŁżń½ŗńäĪµÅ┤’╝īµ▓Æõ║║Õć║ķØóÕłČµŁóŃĆéÕ橵ü®õŠåķÖĘÕģźÕŹüÕłåÕŹ▒ķܬÕóāÕ£░’╝īķĆÖµÖéµ£ēĶ╗ŹķĀŁńÖ╝µĆÆ’╝īńø┤µÄźÕĖČÕģĄķĆ▓Õ¤ÄõĖŹķĪ¦õĖĆÕłćµÉȵĢæÕ橵ü®õŠå’╝īÕĖČķā©ķÜŖńø┤µÄźķ¢ŗµ¦ŹÕ░ćÕ橵ü®õŠåÕŠ×ń┤ģĶĪøÕģĄńĄäń╣öńÜäÕ£ŹÕø░õĖŁµÉȵĢæÕć║õŠåŃĆé
ķĆÖõĖĆķćŹÕż¦õ║ŗõ╗ČÕ«śµ¢╣ÕŠ×õŠåõĖŹµÅÉ’╝īķä¦ń®ÄĶČģÕø×µåČķīäõ╣¤õĖŹµÅÉ’╝īõ╝╝õ╣ĵ£ēµäÅķÜ▒ń××Ķ«ōÕ«āµłÉńé║õĖĆÕĆŗÕģ½ÕŹ”µĄüÕé│ńÜäµĢģõ║ŗŃĆéĶĆīõ║ŗÕŠīÕ橵ü®õŠåÕ£©µÄźĶ”ŗÕż¢Ķ│ōÕ¤āÕĪ×õ┐äµ»öõ║×ńÜćÕĖصÖé’╝īĶ½ćÕł░µ¢ćķØ®Ķó½Õ£ŹÕø░µö╗µōŖµÖé’╝īµÅÉÕł░ķĆÖõĖĆõ║ŗõ╗Č’╝īÕæ©Ķ¬¬µłæĶó½Õ£ŹÕø░ĶĪصōŖ’╝īµ£ēõ║║ń¤źķüōÕŠī’╝īÕĖČÕģĄķĆ▓Õ¤ÄĶ¦ŻµĢæõ║åµłæ’╝īķ¢ŗõ║嵦ŹµŁ╗õ║åõ║║ŃĆé
ķĆÖķćīÕ░▒Õ╝ĢńÖ╝õĖĆń│╗ÕłŚńÜäń¢æÕĢÅ’╝Ü
’Į×µ»øĶłć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é║õ╗Ćķ║╝µ▓Ƶ£ēĶ┐Įń®Čµü»õ║ŗÕ»¦õ║║õ║å’╝¤
’Į×õ╗Ćķ║╝õ║║ĶåĮÕż¦Õ”äńé║ÕÅ»õ╗źÕĖČÕģĄķĆ▓Õ¤ÄĶĆīõĖöķ¢ŗµ¦ŹµŁ╗õ║åõ║║’╝¤
’Į×Õ«śµ¢╣ńé║õ╗Ćķ║╝Ķ”üķÜ▒ń××’╝īµēƵ£ēńĢČõ║ŗõ║║ķāĮķÜ╗ÕŁŚõĖŹµÅÉ’╝īĶ«ōÕ«āµłÉń½ŗõĖĆÕĆŗµ▒¤µ╣¢Õģ½ÕŹ”µĄüÕé│’╝¤
’Į×Õ”éµ×£µś»µ£ēõ║║ķĆĀĶ¼Ā’╝īÕ«śµ¢╣Õ«īÕģ©ÕÅ»õ╗źÕ£©ńøĖķŚ£µ¢ćķØ®µ¢ćõ╗ČõĖŁķĆ▓ĶĪīķü┐Ķ¼Ā’╝īÕŹ╗ĶüĮõ╣ŗõ╗╗õ╣ŗŃĆé
’Į×ķĆÖµś»Õ橵ü®õŠåĶłćµ¢ćķØ®Õ░ÅńĄä’╝łµ»øµŠżµØ▒’╝ēµ¢ćķØ®Ķ¦ÆÕŖøõĖŁ’╝īµ»øĶłćµ¢ćķØ®Õ░ÅńĄäÕö»õĖĆķĆĆńĖ«ķĆĆĶ«ōńÜäõĖƵ¼Ī’╝īÕæ©Õģ©Ķ║½ĶĆīķĆĆ’╝īµ▓Ƶ£ēõ╗╗õĮĢõ║║ķüŁÕÅŚĶÖĢÕłåĶ┐ĮĶ▓¼ŃĆé
’Į×ĶĆī1970Õ╣┤µ»øµŠżµØ▒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ń░ĮńÖ╝ŃĆīµĖģń«Ś516ÕÅŹķØ®ÕæĮķøåÕ£śŃĆŹķüŗÕŗĢ’╝īµø┤µś»Õ橵ü®õŠåÕż¦ńŹ▓Õģ©ÕŗØńÜäµ│©Ķģ│ŃĆé
’╝ł’Į×ķŁüń£üÕ▒▒Õ»©’╝ē
ŃĆīķ”¢ķāĮ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ń║óÕŹ½ÕģĄÕøóŃĆŹ’╝īõ╗¢õ╗¼ńÜäõĖ╗Ķ”üµ┤╗ÕŖ©µś»Õ╝ĀĶ┤┤ÕÅŹÕ»╣Õ橵ü®µØźńÜäµĀćĶ»ŁÕÆīÕż¦ÕŁŚµŖźŃĆéõ╗¢õ╗¼Ķ┐śµ£ēõĖĆÕźŚńŗ¼ńē╣ńÜäŌĆ£ńÉåĶ«║ŌĆØ’╝Üõ╗ĵ×üŌĆ£ÕĘ”ŌĆص¢╣ķØóÕɔիÜŌĆ£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ŌĆØŃĆéĶ«żõĖ║ŌĆ£µ¢ćķØ®ŌĆصś»ŌĆ£Õģ©ÕøĮµĆ¦ńÜäÕÅŹķØ®ÕæĮµö┐ÕÅśŌĆØ’╝īŌĆ£Ķć│õ╗ŖĶ┐śķÜÉĶŚÅÕ£©ÕøĮÕ«Čķ”¢Ķäæµ£║Õģ│µÄīµÅĪÕż¦µØāńÜäÕłśķéōõ╗ŻńÉåõ║║Õ£©ń╗¤õĖƵīćµīźńØĆĶ┐ÖÕ£║Õģ©ÕøĮµĆ¦ńÜäÕÅŹķØ®ÕæĮµö┐ÕÅśŌĆØ’╝īÕ╣ČĶ«żõĖ║ŌĆ£µ¢ćÕī¢ķØ®ÕæĮµś»õ║īń║┐ÕÉæõĖĆń║┐Õż║µØāŌĆØ’╝īÕøĀµŁżõ╗¢õ╗¼Ķ”üŌĆ£ÕÉæõĖŁÕż«Õż║µØāŌĆØ’╝īŌĆ£ÕĮ╗Õ║ĢķØ®ÕæĮŌĆØŃĆé
ń╗äń╗浳Éń½ŗÕÉÄ’╝īõ╗¢õ╗¼µŖŖń╗äń╗ćÕż┤ńø«Õ╝ĀÕ╗║µŚŚõĖżõĖ¬µ£łÕēŹÕåÖńÜäŃĆŖń╗ÖÕ橵Ć╗ńÉåńÜäõĖĆÕ░üÕģ¼Õ╝Ćõ┐ĪŃĆŗµŖ䵳ÉÕż¦ÕŁŚµŖź’╝īÕģ¼Õ╝ĆĶ┤┤Õ£©ķÆóķÖóŃĆéÕż¦ÕŁŚµŖźń¦░Õ橵ü®µØźµś»ŌĆ£õ║īµ£łķ╗æķŻÄńÜäµĆ╗ÕÉÄÕÅ░ŌĆØŃĆüŌĆ£µÉ×ĶĄäµ£¼õĖ╗õ╣ēÕżŹĶŠ¤ŌĆØŃĆé
õĖĵŁżÕÉīµŚČ’╝īÕīŚõ║¼Õå£õĖÜÕż¦ÕŁ”õ╣¤Õć║ńÄ░õ║åõĖĆõĖ¬Õģ¼Õ╝Ćń髵ēōÕ橵ü®µØźńÜä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ŃĆéÕ£©ÕīŚõ║¼ń¼¼õ║īÕż¢ÕøĮĶ»ŁÕŁ”ķÖó’╝īõ╗źÕ╝ĀÕģēµŁ”õĖ║ķ”¢ńÜäõĖĆõ║øõ║║Õģ¼Õ╝ĆÕÅæĶĪ©ķÆłÕ»╣Õ橵ü®µØźńÜäŌĆ£Õ╝Ćńé«ÕŻ░µśÄŌĆØ’╝īÕŻ░ń¦░Ķ”üµÅ¬Õć║µ¢░ńÜäĶĄäõ║¦ķśČń║¦õ╗ŻĶĪ©õ║║ńē®ŃĆéÕīŚõ║¼Õż¢ÕøĮĶ»ŁÕŁ”ķÖó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صŖøÕć║Õż¦ÕŁŚµŖźŃĆŖµł│ń®┐õĖĆõĖ¬Õż¦ķś┤Ķ░ŗŃĆŗ’╝īĶ»┤Õ橵ü®µØźµś»ŌĆ£ÕÅŹķØ®ÕæĮõĖżķØóµ┤ŠŌĆØŃĆéõ╣ŗÕÉÄĶ┐Öõ║øÕÅŹÕæ©ńÜäÕģĄÕøóÕÉłµĄü’╝īµłÉõĖ║ŌĆ£ķ”¢ķāĮ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ń║óÕŹ½ÕģĄÕøóŌĆØŃĆé
ķĆÖõ║øĶĪīÕŗĢńÜäĶāīÕŠīķāĮµ£ē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ńÜäÕĮ▒ÕŁÉ’╝īń║ĄÕ«╣µö»µīüńÜäÕŠīÕÉÄÕ░▒µś»µ¢ćķØ®Õ░ÅńĄä’╝īÕ░▒µś»µ▒¤ķØÆ’╝īĶĆīµ▒¤ĶāīÕÉĵś»Ķ¬░’╝īķØ×ÕĖĖµśÄńó║’╝īÕĘ▓ńČōõĖŹńö©Ķ¬¬õ║åŃĆé
1967Õ╣┤8µ£ł9µŚź’╝ī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╝ĆÕ▒Ģõ║åõĖĆõĖ¬µēĆĶ░ōŌĆ£Õģ½┬Ęõ╣صłśÕĮ╣ŌĆØ’╝īõ╗¢õ╗¼µ┤ŠÕć║õĖĆÕż¦µē╣õ║║Õæś’╝īÕ£©ÕćīµÖ©ńÜ䵌ČÕĆÖ’╝īÕł░ÕīŚõ║¼ÕŖ©ńē®ÕøŁŃĆüńöśÕ«ČÕÅŻÕĢåÕ£║ŃĆüĶź┐ÕøøõĖüÕŁŚĶĪŚńŁēÕżäÕż¦ķćŵĢŻÕÅæŃĆüÕ╝ĀĶ┤┤ÕÅŹÕæ©õ╝ĀÕŹĢ’╝īµČéÕåÖÕÅŹÕ橵ĀćĶ»ŁŃĆéĶ┐Öõ║øõ╝ĀÕŹĢÕÆīµĀćĶ»Łķóśńø«µś»’╝ÜŃĆŖµÅ¬Õć║õ║īµ£łķ╗æķŻÄńÜäµĆ╗ÕÉÄÕÅ░ŃĆŗŃĆüŃĆŖÕ橵ü®µØźńÜäĶ”üÕ«│µś»ĶāīÕÅø5┬Ę16ķĆÜń¤źŃĆŗŃĆüŃĆŖÕ橵ü®µØźµś»µ»øµ│ĮõĖ£õĖ╗õ╣ēńÜäÕÅ»ĶĆ╗ÕÅøÕŠÆŃĆŗńŁēŃĆéĶ┐Öõ║øõ╝ĀÕŹĢÕÆīµĀćĶ»ŁÕØćńĮ▓ÕÉŹŌĆ£ķ”¢ķāĮ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ń║óÕŹ½ÕģĄÕøóŌĆØŃĆ鵣żÕÉÄŌĆ£õĖŁÕż«µ¢ćķØ®ŌĆØõĖŹÕŠŚõĖŹµ┤ŠÕć║ķÖłõ╝»ĶŠŠńŁēõ║║Õć║ķØóĶĪ©ńż║’╝ÜÕ橵Ć╗ńÉåµś»µ»øõĖ╗ÕĖŁÕÅĖõ╗żķā©ńÜäõ║║’╝īµś»µ»øõĖ╗ÕĖŁŃĆüµ×ŚÕē»õĖ╗ÕĖŁõ╣ŗõĖŗµĆ╗ń«Īõ║ŗÕŖĪńÜäÕÅéĶ░ŗ’╝īÕÅŹÕ»╣Õ橵Ć╗ńÉåµś»õĖźķćŹńÜäµö┐µ▓╗ķŚ«ķóśŃĆé
õĖĵŁżÕÉīµŚČ’╝īÕĮōµŚČÕÅæńö¤ÕćĀõ╗ČķćŹĶ”üńÜäõ║ŗµāģ’╝īõĖĆõ╗ȵś»ŃĆŖń║󵌌ŃĆŗµØéÕ┐ŚÕłŖÕÅæõ║åń╗ÅÕģ│ķöŗÕ«ĪÕ«ÜńÜäńżŠĶ«║ŃĆŖµŚĀõ║¦ķśČń║¦Õ┐ģķĪ╗ńēóńēóµÄīµÅĪµ×¬µØåÕŁÉŃĆŗŃĆéńżŠĶ«║µÅÉÕć║’╝ÜŌĆ£Ķ”üµŖŖÕåøÕåģõĖĆÕ░ŵƫĶĄ░ĶĄäµ£¼õĖ╗õ╣ēķüōĶĘ»ńÜäÕĮōµØāµ┤ŠµÅŁķ£▓Õć║µØźŃĆéŌĆØń¼¼õ║īõ╗ȵś»’╝īõĖŁÕż«µ¢ćķØ®µłÉÕæśńÄŗÕŖøÕÅæĶĪ©õ║åńø┤µÄźķÆłÕ»╣Õ橵ü®µØźńÜäŌĆ£Õģ½┬ĘõĖāĶ«▓Ķ»ØŌĆØ’╝īÕÅĘÕÅ¼Õż¢õ║żķā©ńÜäķĆĀÕÅŹµ┤ŠÕż║µØāŃĆé
ńÄŗÕŖøŃĆüÕģ│ķöŗŃĆüµłÜµ£¼ń”╣ÕÉī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ńÜäńø«µĀ浜»õĖĆĶć┤ńÜä’╝īÕŹ│ķāĮµŖŖń¤øÕż┤µīćÕÉæÕ橵ü®µØźÕÆīõĖĆÕż¦µē╣ĶĆüÕ╣▓ķā©ŃĆéÕĮōµŚČÕÉäń║¦Õģܵö┐µ£║Õģ│Õżäõ║Äńś½ńŚ¬ńŖȵĆü’╝īÕö»õĖĆĶāĮÕ»╣ķĆĀÕÅŹµ┤Šń╗äń╗ćÕÅæÕÅʵ¢Įõ╗żńÜ䵜»õĖŁÕż«µ¢ćķØ®’╝ī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ģĄÕøóõ╣ŗµēĆõ╗źµ»½µŚĀķĪŠÕ┐īÕÅŹÕ橵ü®µØź’╝īµśŠńäČõĖÄõĖŁÕż«µ¢ćķØ®µłÉÕæśńÄŗÕŖøŃĆüÕģ│ķöŗŃĆüµłÜµ£¼ń”╣ńÜäń║ĄÕ«╣ŃĆüµö»µīüõĖŹµŚĀÕģ│ń│╗ŃĆé
1967Õ╣┤µłÜµ£¼ń”╣Õģ¼Õ╝ĆĶ»┤’╝ܵ»øõĖ╗ÕĖŁÕÅĖõ╗żķā©ÕŬµ£ēõ║öõĖ¬õ║║’╝īĶ┐Öõ║öõĖ¬õ║║µś»õĖ╗ÕĖŁŃĆüµ×ŚµĆ╗ŃĆüõ╝»ĶŠŠŃĆüÕ║Ęńö¤ŃĆüµ▒¤ķØÆŃĆéÕģ¼ńäȵŖŖÕ橵ü®µØźµÄÆķÖżÕ£©ŌĆ£µ»øõĖ╗ÕĖŁÕÅĖõ╗żķā©ŌĆØõ╣ŗÕż¢’╝īĶĆīĶ┐Öõ╣¤µśŠńäȵś»µ£ēÕŠīÕÅ░ńÜäŃĆé
µ£ēõ║║Ķ¬¬ķĆÖµś»µ»øµ│ĮõĖ£õĖŹĶāĮÕ«╣Õ┐ŹńÜä’╝īÕøĀõĖ║ŌĆ£µ¢ćÕī¢Õż¦ķØ®ÕæĮŌĆØńÜäńø«ńÜ䵜»Ķ”üµĢ┤ÕģÜÕåģĶĄ░ĶĄäµ┤Š’╝īĶĆīõĖŹµś»Ķ”üµēōÕĆƵēƵ£ēńÜäĶĆüÕ╣▓ķā©ŃĆéõ╣ŗÕÉÄńÄŗŃĆüÕģ│ŃĆüµłÜĶó½ÕĮōµłÉ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ÕģĄÕøóŌĆØÕÉÄÕÅ░µŖōĶĄĘµØźŃĆéõĖŹõ╣ģ’╝īµ»øµ│ĮõĖ£ÕÉæķĆĀÕÅŹµ┤ŠÕÅæÕć║ÕÅĘÕż’╝ÜķØ®ÕæĮńÜäÕŁ”ńö¤Ķ”üÕøóń╗ōÕģ▒ÕÉīµēōÕ׫ÕÅŹķØ®ÕæĮķś┤Ķ░ŗķøåÕøó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ŃĆ鵣żÕÉÄÕģ©ÕøĮõĖĆÕŹāÕøøńÖŠÕżÜõĖ¬ķĆĀÕÅŹµ┤Šń╗äń╗ćõĖżõĖćÕżÜõ║║’╝īÕ£©ÕīŚõ║¼ķÆóķōüÕŁ”ķÖóÕżÕ╝ĆŌĆ£ÕĮ╗Õ║ĢńĀĖńāéÕÅŹÕŖ©ń╗äń╗ćŌĆśķ”¢ķāĮõ║ö┬ĘõĖĆÕģŁķ╗æÕī¬ÕģĄÕøóŌĆÖÕż¦õ╝ÜŌĆØ’╝īÕ╝ĀÕ╗║µŚŚńŁēõ║öõĖ¬ŌĆ£õ║ö┬ĘõĖĆÕģŁŌĆØÕż┤ńø«Ķó½µÅ¬Õć║ńż║õ╝ŚŃĆé ĶĆīķĆÖõĖĆķ½śĶČģńÜäµēŗµ│Ģõ╣¤ÕŬµ£ēµēŹµ£ēÕüēÕż¦ķĀśĶó¢µēŹÕģĘÕéÖķĆÖµ©ŻńÜäĶ¼ĆńĢźŃĆé
µłæµā│µłæÕĆæķāĮÕÅ»õ╗źÕŠ×õĖŁń£ŗÕć║ńĢČÕ╣┤ńÜäķ¼źńłŁĶ░ŗńĢź’╝īķøÖµ¢╣õ║ÆńøĖµÄ©µēŗĶ¦ÆÕŖøńÜäĶĪĪķćÅ’╝īń£ŗÕ«śĶć¬ńäȵ£āµ£ēÕÉäĶ欵ĖģķåÆńÜäµĆØĶĆāĶłćĶ¬ŹĶŁśŃĆé
µłæńÜäķøȵś¤Ķ©śµåČ’╝Ü
ŃĆīµĖģµ¤ź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ÅŹķØ®ÕæĮķøåÕ£śķüŗÕŗĢ’╝īµÖéķ¢ōĶĘ©Õ║”ÕŠłķĢĘ’╝īµĀ╣µōÜńÅŠÕ£©Õģ¼ÕĖāńÜäĶ│ćµ¢ÖķĪ»ńż║’╝īķĆÖÕ«īÕģ©Õ░▒µś»µīæÕŗĢńŠżń£Šµ¢ŚńŠżń£Š’╝īÕƤµ®¤Ķ┐½Õ«│µĢ┤õ║║ńÜäµö┐µ▓╗ķüŗÕŗĢ’╝īÕ«āµ│óÕÅŖÕģ©Õ£ŗ’╝īķĆĀµłÉńÜäĶ┐½Õ«│ĶłćÕåżÕüćķī»µĪłńöÜÕżÜńöÜÕ╗ŻŃĆé
ŃĆīµ¢ćķØ®µÖéµ£¤ŃĆŹµłæÕĘ▓Ķ©śõ║ŗ’╝īĶ”ŗĶŁēõ║åµē╣µ¢Śµ£ā’╝īńŠżń£ŠķĆĀÕÅŹµ┤ŠķøÖµ¢╣µŁ”µ¢ŚÕĀ┤µÖ»’╝īńöÜĶć│µ£ēõĖƵ¼ĪĶó½Õø░Õ£©µłæµ»ŹĶ”¬Õ¢«õĮŹńÅŠÕĀ┤’╝īĶ”¬ń£╝ńø«ńØ╣µŁ”µ¢ŚńÅŠÕĀ┤ńÜäńē浫Ą’╝īµ£ēõĖƵ¼ĪķÉĄĶĘ»Õż¦µ©ōĶó½ń¬üńäČÕø┤µö╗’╝īµĢ┤ÕĆŗµŁ”µ¢Śµö╗ķś▓Õż¦µæ¤ķćīÕ░▒µłæõĖĆÕĆŗÕ░ÅÕŁ®’╝īĶ║▓Õ£©õĖĆķéŖĶ¦ÆĶÉĮÕüĘÕüĘń£ŗ’╝īńÅŠÕĀ┤Õż¦µ©ōķćīÕ╣│µÖ鵳æń£╝õĖŁńÜäõ╝»õ╝»ŃĆüÕÅöÕÅöŃĆüķś┐Õ¦©ŃĆüÕż¦ÕōźÕōźŃĆüÕż¦Õ¦ÉÕ¦ÉÕĆæ’╝īķĆÖÕĆŗµÖéÕĆÖµś»ńé║õ║åĶ欵łæõ┐ØĶŁĘĶłćĶć¬ĶĪø’╝īõ╗¢ÕĆæńÜäÕŗćńīøÕ£śńĄÉń▓Šńź×’╝īõ║ÆńøĖķģŹÕÉłõ┐ØĶŁĘµł░µ¢ŚńÜäń▓Šńź×’╝īÕŠ×Õ░ÅÕ░▒µĘ▒µĘ▒µżŹÕģźõ║åµłæńÜäĶģ”µĄĘŃĆéķĆÖõ╣¤µś»ķÉĄĶĘ»µāģńĄÉńÜäńö▒õŠå’╝īµ¢ćķØ®µÖéµ£¤ķÉĄĶĘ»ÕŁÉÕ╝¤µŖ▒Õ£śÕ░ŹÕż¢ķó©µ░Ż’╝īÕÅ»õ╗źĶ¬¬µś»ķÉĄĶĘ»ÕŁÉÕ╝¤ÕŁĖµĀĪńÜäŃĆīµĀĪķó©µĀĪĶ©ōŃĆŹ’╝īµłæÕĆæńÜäÕż¦ÕōźÕż¦Õ¦ÉÕ░▒µś»ķĆÖµ©ŻÕĖČĶæŚµłæÕĆæĶĄ░ķĆ▓µ▒¤µ╣¢’╝īĶĆīµłæÕĆæĶĄ░ķĆ▓ńżŠµ£āÕÉÄ’╝īõ╣¤ÕÉīµ©Żµś»ķĆÖµ©ŻńÜäµģŗÕ║”õ┐ØĶŁĘµłæÕĆæńÜäķÉĄĶĘ»Õ░ÅÕ╝¤Õ╝¤Õ░ÅÕ”╣Õ”╣ÕĆæŃĆé
µłæÕ░Ź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ķüŗÕŗĢńÜäĶ©śµåČ’╝īµś»ÕŹ░Ķ▒ĪõĖŁµ¤ÉõĖĆÕż®µÖÜķŻ»ńłĖńłĖµ»öÕ╣│ÕĖĖÕø×õŠåńÜäĶ”üµÖÜ’╝īÕøĀńé║ńłĖńłĖõĖŹÕø×Õ«Č’╝īµłæÕĆæµś»õĖŹķ¢ŗķŻ»ńÜäŃĆéńłĖńłĖÕø×Õ«ČÕÉĵłæÕĆæÕø┤µĪīÕÉāķŻ»’╝īÕ░▒ĶüĮńłĖńłĖÕ░ŹÕ¬ĮÕ¬ĮĶ¬¬’╝īĶ¬░Ķ¬░Ķ¬░ŃĆüķÉĄĶĘ»Õ£░ÕŹĆÕÉ䵫ĄķāĮÕ«ŻÕĖāµŖō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łåÕŁÉ’╝īÕ£░ÕŹĆńĖĮķā©ŃĆüÕĘźÕŗÖµ«ĄŃĆüķø╗ÕŗÖµ«Ą’╝īĶ╗ŖÕŗÖµ«ĄŃĆüµ®¤ÕŗÖµ«Ąµ¤Éµ¤Éµ¤ÉķāĮĶó½µŖōõ║å’╝īµś»ŃĆīõ║öõĖĆÕģŁŃĆŹÕłåÕŁÉ’╝īÕøĀńé║µÅÉÕł░ńÜ䵤Éõ║øõ║║ÕÉŹ’╝īÕ¬ĮÕ¬ĮÕŠłÕÉāķ®ÜÕ░ÅĶü▓Ķ¬¬’╝ܵĆÄõ╣łõ╗¢õ╣¤µś»’╝¤µÅÉÕł░ńÜäõ║║µłæõ╣¤µ£ēÕŹ░Ķ▒Ī’╝īõ╣¤µØźĶ┐浳æõ╗¼Õ«ČÕÉāĶ┐ćķźŁ’╝īÕ░ÅÕŁ®õ╣¤õĖŹµĢóÕżÜÕĢÅ’╝īõĮåÕŹ░Ķ▒ĪµĘ▒Õł╗ŃĆéŃĆŹ
’Į×ķŁüń£üÕ▒▒Õ»©┬ĘķŁüń£üĶĆüÕ╝Ą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