гҖҗдёҖеҖӢиІҙе·һиҖҒй„үпјҡжңұеҺҡжҫӨгҖ‘пҪһ йӯҒзңҒеұұеҜЁ
и’ҷеҹҺиҖҒејө-101698 03/15 125444.0/1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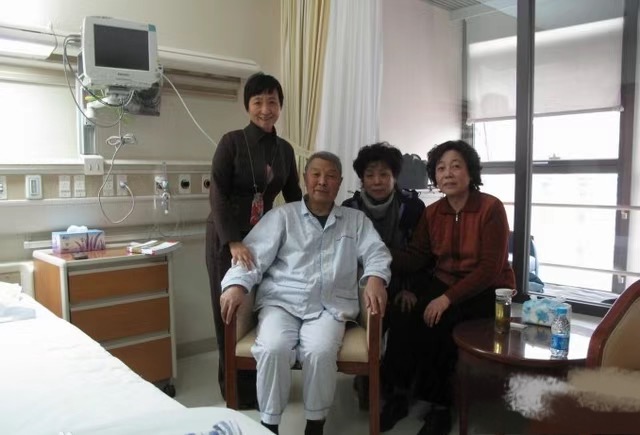




гҖҗдёҖеҖӢиІҙеҚ…иҖҒй„үпјҡжңұеҺҡжҫӨгҖ‘пҪһйӯҒзңҒеұұеҜЁ
жңұеҺҡжҫӨз”ҹе№іпјҡ
жңұеҺҡжҫӨпјҲ1931е№ҙ1жңҲвҖ”2010е№ҙ5жңҲ9ж—ҘпјүпјҢиІҙе·һз№”йҮ‘дәәпјҢдёӯиҸҜдәәж°‘е…ұе’ҢеңӢж”ҝжІ»дәәзү©пјҢеҺҹ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®ЈеӮійғЁйғЁй•·гҖӮдёӯе…ұеҚҒдәҢеұҶеҖҷиЈңдёӯеӨ®е§”е“ЎгҖҒдёӯеӨ®е§”е“ЎгҖӮ
жңұеҺҡжҫӨж–ј1949е№ҙеҠ е…ҘдёӯеңӢе…ұз”ўй»ЁпјҢеҗҢе№ҙиӮ„жҘӯж–јиІҙйҷҪеё«зҜ„еӯёйҷўеҸІең°зі»гҖӮ1964е№ҙеңЁеӣӣжё…йҒӢеӢ•дёӯиў«й–Ӣй»ЁзұҚгҖҒдёӢж”ҫеӢһеӢ•гҖӮ
1978е№ҙе№іеҸҚеҫҢпјҢжӣҫд»»дёӯе…ұиІҙйҷҪеёӮ委жӣёиЁҳзӯүиҒ·гҖӮ
1983е№ҙд»»иІҙе·һзңҒ委жӣёиЁҳпјҢиІ иІ¬з¶“жҝҹе»әиЁӯгҖӮ當е№ҙиІҙе·һзңҒе·ҘжҘӯзёҪз”ўеҖјеўһй•·18%пјҢеҫһиҖҢеј•иө·иғЎиҖҖйӮҰзӯүй«ҳеұӨжіЁж„ҸгҖӮ
1985е№ҙ4жңҲпјҢеҮәд»»иІҙе·һзңҒ委жӣёиЁҳгҖӮеҗҢе№ҙ8жңҲпјҢеҮәд»»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®ЈеӮійғЁйғЁй•·пјҢжҲҗзӮәиғЎиҖҖйӮҰзҡ„йҮҚиҰҒеҠ©жүӢгҖӮеңЁд»»жңҹй–“пјҢд»–жӣҫжҸҗеҮәгҖҢдёүеҜ¬и«–гҖҚпјҲеҜ¬еҺҡгҖҒеҜ¬е®№гҖҒеҜ¬й¬Ҷпјүж–№йҮқпјҢд»Ҙж”ҫеҜ¬е°Қж–Үи—қз•ҢиҲҮеӯёиЎ“з•Ңзҡ„йҷҗеҲ¶гҖӮ
1987е№ҙ2жңҲеңЁеҸҚе°ҚиіҮз”ўйҡҺзҙҡиҮӘз”ұеҢ–йҒӢеӢ•дёӯиў«и§ЈиҒ·пјҢж”№д»»еңӢеӢҷйҷўиҫІжқ‘зҷјеұ•з ”究дёӯеҝғеүҜдё»д»»пјҢеҫҢеңЁдёӯе…ұеҚҒдёүеӨ§дёҠиҗҪйҒёдёӯеӨ®е§”е“ЎгҖӮ
1988е№ҙпјҢи¶ҷзҙ«йҷҪеүөйҖ ж©ҹжңғдҪҝе…¶еҫ©еҮәпјҢж–јжҳҜд»–еҸҲж“”д»»е…ЁеңӢзёҪе·Ҙжңғ第дёҖеүҜдё»еёӯгҖҒжӣёиЁҳиҷ•з¬¬дёҖжӣёиЁҳгҖӮ
1989е№ҙ12жңҲиў«е…ҚеҺ»й ҳе°ҺиҒ·еӢҷгҖӮ
2010е№ҙ5жңҲ9ж—ҘеҮҢжҷЁеӣ з—…еңЁеҢ—дә¬йҖқдё–гҖӮ
2014е№ҙпјҢгҖҠжңұеҺҡжҫӨж–ҮеӯҳгҖӢз”ұеҢ—дә¬дё–з•Ңең–жӣёеҮәзүҲе…¬еҸёзҷјиЎҢ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пјҢдёӯе…ұжӯ·еҸІдёҠйӣЈеҫ—дёҖдҪҚдёӯеҸІе®ЈеӮійғЁгҖҢдёүеҜ¬гҖҚйғЁй•·гҖӮ
вҖңе…ҡеӘ’姓е…ҡвҖқпјҢвҖңдёҚеҫ—еҰ„и®®дёӯеӨ®вҖқжҳҜиҝҷдәӣе№ҙжіӣж»ҘжҲҗзҒҫзҡ„ж”ҝжІ»жңҜиҜӯпјҢд№ҹжҳҜдёӯе…ұдёҘжҺ§ж–°й—»зҰҒй”ўжҖқжғіиЁҖи®әзҡ„зңҹе®һеҶҷз…§пјҢеҪ“еӘ’дҪ“жІҰдёәе–үиҲҢе’Ңе·Ҙе…·пјҢеӨ§еҮЎе…¬ејҖзӣ‘зқЈжү№иҜ„дёӯе…ұд»ҘеҸҠйўҶеҜјдәәйғҪиў«и§ҶдёәеӨ§йҖҶдёҚйҒ“пјҢжҲ–е®ҡзҪӘе…ҘзӢұжҲ–йҒӯзӣ‘зҰҒжҲ–иў«зҰҒиЁҖпјҢи®ёеӨҡдәәеёёеёёжғіиө·дёӯе…ұеүҚдёӯе®ЈйғЁй•ҝжңұеҺҡжіҪжӣҫз»ҸиҜҙиҝҮзҡ„иҜқпјҡвҖңд»ҺиҫӣдәҘйқ©е‘ҪеҲ°д»ҠеӨ©пјҢжҲ‘们иҪ¬дәҶдёҖеңҲпјҢеҸҲиҪ¬еӣһеҲ°дәҶдё“еҲ¶зҡ„иө·зӮ№пјҢиҖҢдё”иҝҷдёӘдё“еҲ¶и¶…иҝҮд»»дҪ•дёҖдёӘжңқд»ЈпјҢе…¶жҺ§еҲ¶зҡ„дёҘй…·еүҚж— еҸӨдәәпјҢе…¶еҜ№жҖқжғізҡ„й’іеҲ¶и¶…иҝҮеҺҶд»ЈпјҢзӣёжҜ”д№ӢдёӢпјҢиҝҮеҺ»йӮЈдәӣж–Үеӯ—зӢұз®—дёҚеҫ—д»Җд№ҲгҖӮвҖқ
дәһжҙІе‘ЁеҲҠеңЁ2013е№ҙ5жңҲзү№еҲҘзҷјиЎЁе°Ҳ欄е ұйҒ“ж–Үз« гҖҠжңұеҺҡжҫӨе°Қдёӯе…ұй«”еҲ¶жү№еҲӨгҖӢпјҢеңӢе…§и®ҖиҖ…иў«еұҸи”ҪгҖӮ
гҖҠжңұеҺҡжҫӨж–ҮйҒёгҖӢеңЁйҰҷжёҜеҮәзүҲпјҢиЁҳйҢ„дәҶйҖҷдҪҚеүҚдёӯе®ЈйғЁй•·зҡ„жҖқжғіжҲҗжһңпјҢжҢҮдёӯе…ұж”ҝжІ»е°ҲеҲ¶пҪӨ經жҝҹзҷјеұ•пҪӨиҲҮеңӢйҡӣеҸҚеӢ•еӢўеҠӣзөҗзӣҹпјҢеҸҜиғҪж·ӘзӮәйӮӘжғЎеҠӣйҮҸпјӣиҖҢж”№йқ©й–Ӣж”ҫе°ұжҳҜеӣһжӯёдәәйЎһе…ұеҗҢж–ҮжҳҺзҡ„еӨ§йҒ“гҖӮ
дәәй–“з—ӣеӮ·еҲҘпјҢжӯӨжҳҜй•·еҲҘиҷ•гҖӮдә”жңҲд№қж—ҘжҳҜеүҚ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®ЈеӮійғЁй•·жңұеҺҡжҫӨйҖқдё–дёүйҖұе№ҙзҙҖеҝөж—ҘгҖӮжңұеҺҡжҫӨиў«иӯҪзӮәгҖҢдёӯе…ұй»Ёе…§ж°‘дё»жҙҫзҡ„йқҲйӯӮдәәзү©гҖҚгҖҒгҖҢгҖҺиө°еҫ—жңҖйҒ гҖҒзңӢеҫ—жңҖйҖҸгҖҸзҡ„дёӯе…ұж°‘дё»жҙҫиүҜеҝғжҖқжғіе®¶гҖҚпјҢеңЁд»»дёӯе®ЈйғЁй•·жңҹй–“жҸҗеҮәзҹҘеҗҚзҡ„гҖҢдёүеҜ¬ж”ҝзӯ–гҖҚпјҢд»–жң¬дәәд№ҹиў«зЁұзӮәгҖҢдёүеҜ¬йғЁй•·гҖҚгҖӮйҖҷгҖҢдёүеҜ¬гҖҚжҳҜеҜ¬еҺҡгҖҒеҜ¬е®№е’ҢеҜ¬й¬ҶгҖӮз”Ёд»–зҡ„и©ұиӘӘпјҢгҖҢе°Қж–ји·ҹжҲ‘еҖ‘еҺҹдҫҶзҡ„жғіжі•дёҚеӨӘдёҖиҮҙзҡ„жҖқжғіи§Җй»һ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жҺЎеҸ–еҜ¬е®№дёҖй»һзҡ„ж…ӢеәҰпјӣе°Қеҫ…жңүдёҚеҗҢж„ҸиҰӢзҡ„еҗҢеҝ—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еҜ¬еҺҡдёҖй»һпјӣж•ҙеҖӢз©әж°ЈгҖҒз’°еўғжҳҜ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жҗһеҫ—еҜ¬й¬ҶгҖҒжңүеҪҲжҖ§дёҖй»һгҖҚгҖӮеңЁд»–йҖқдё–дёүйҖұе№ҙд№ӢйҡӣпјҢд»–зҡ„гҖҠй—ңж–јиҝ‘зҸҫд»ЈдёӯеңӢи·Ҝеҫ‘йҒёж“Үзҡ„жҖқиҖғвҖ”вҖ”жңұеҺҡжҫӨж–ҮйҒёгҖӢпјҲдёӢзЁұгҖҠж–ҮйҒёгҖӢпјүеңЁйҰҷжёҜз”ұжәҜжәҗжӣёзӨҫеҮәзүҲгҖӮи©ІжӣёзІҫйҒёдәҶжңұеҺҡжҫӨеӨҡзҜҮйҮҚиҰҒи‘—иҝ°еҸҠиЁӘи«ҮпјҢдёҚе°‘еҝ иЁҖи®ңи«–пҪӨдёҖдәӣйҮҚиҰҒе…§е®№йҰ–еәҰзҚЁе®¶жҠ«йңІгҖӮе®ғеҖ‘иЁҳйҢ„дәҶйҖҷдҪҚжҖқжғіиҖ…е°ҚдёӯеңӢе•ҸйЎҢгҖҒдёӯеңӢйҒ“и·Ҝзҡ„жҖқиҖғпјҢд»ЈиЎЁдәҶжӣҫ經дҝЎд»°йқ©е‘ҪгҖҒеҸҲеҫһзҙ…иүІжҘөж¬Ҡй«”еҲ¶дёӯжңҖзөӮеҸҚеҸӣиҖҢеҮәзҡ„дёҖд»Јдәәзҡ„жҖқжғіжҲҗе°ұгҖӮжңұеҺҡжҫӨеңЁжӣёдёӯжҢҮеҮәпјҢдәҢеҚҒдё–зҙҖдёӯеңӢе…ұз”ўдё»зҫ©йқ©е‘ҪеҸҠе…¶йҖ е°ұзҡ„зҙ…иүІжҘөж¬Ҡй«”еҲ¶пјҢеҒҸйӣўдәҶдәәйЎһж–ҮжҳҺзҡ„жӯЈйҒ“гҖӮд»–еӨ§иҒІз–ҫе‘јиҰҒжҚҚиЎӣжҷ®дё–еғ№еҖјпјҢеҸҚе°Қй–Ӣжӯ·еҸІеҖ’и»ҠпјҡгҖҢж”№йқ©й–Ӣж”ҫе°ұжҳҜеӣһжӯёдәәйЎһж–ҮжҳҺзҡ„е…ұеҗҢеӨ§йҒ“пјҒеӣһжӯёжӯ·еҸІпјҒеӣһжӯёеёёиӯҳпјҒеӣһжӯёдәәйЎһе…ұеҗҢеғ№еҖјпјҒгҖҚ
жңұеҺҡжҫӨе°ҚдёӯеңӢ當дёӢзҸҫеҜҰзҡ„жү№еҲӨдёҖйҮқиҰӢиЎҖпјҢд»–зӣҙиЁҖгҖҢйҖҷзЁ®ж”ҝжІ»е°ҲеҲ¶гҖҒ經жҝҹзҷјеұ•зҡ„жЁЎејҸпјҢе°ҲеҲ¶ж”ҝж¬ҠиҲҮеӨ–дҫҶиіҮжң¬еӢҫзөҗпјҢжңүеҸҜиғҪдҪҝдёӯеңӢзҷјеұ•жҲҗзӮәеҗҢеңӢйҡӣдёҠдёҖдәӣеҸҚеӢ•еӢўеҠӣзөҗзӣҹзҡ„жңҖйӮӘжғЎеӢўеҠӣгҖӮдәҢеҚҒдё–зҙҖзҡ„иҳҮиҒҜжЁЎејҸгҖҒеҚҒжңҲзӨҫжңғдё»зҫ©йқ©е‘ҪйҒ“и·ҜпјҢжңҖзөӮзөҰжң¬еңӢе’Ңдё–з•Ңеё¶дҫҶжӮІеҠҮжҖ§еҫҢжһңгҖӮдәҢеҚҒдёҖдё–зҙҖзҡ„дёӯеңӢйҒ“и·Ҝе’ҢдёӯеңӢжЁЎејҸпјҢжҳҜж”ҫд№Ӣеӣӣжө·зҡҶжә–зҡ„иө°еҗ‘е№ёзҰҸгҖҒж°‘дё»гҖҒиҮӘз”ұгҖҒжі•жІ»зҡ„еңӢ家зҡ„жҲҗеҠҹ經驗пјҢйӮ„жҳҜжңҖзөӮе°ҮзөҰжң¬еңӢе’Ңдё–з•Ңеё¶дҫҶжӮІеҠҮеҫҢжһңпјҹйҖҷе°ҮжҳҜдәәйЎһеҜҰиёҗе’ҢзҗҶи«–дёҠзҡ„дёҖе ҙеӨ§зҲӯи«–пјҢйҖҷе ҙеӨ§зҲӯи«–жңүеҸҜиғҪиІ«з©ҝж•ҙеҖӢдәҢеҚҒдёҖдё–зҙҖгҖҚгҖӮ
ж“ҡжӮүпјҢйҖҷжҳҜжңұеҺҡжҫӨеңЁдё–еҸҠйҖқдё–еҫҢжө·е…§еӨ–е…¬й–ӢеҮәзүҲзҡ„第дёҖйғЁж”ҝжІ»и‘—дҪңгҖӮи©Іжӣёе°ҺиЁҖйҖҸйңІдәҶжңұеҺҡжҫӨи‘—иҝ°йҒІйҒІжІ’жңүеҮәзүҲзҡ„з·Јз”ұгҖӮгҖҢз”ұж–јеҺҡжҫӨе…Ҳз”ҹгҖҺе®ҡдҪҚгҖҸдёҠзҡ„жҹҗзЁ®зү№ж®ҠжҖ§вҖ”вҖ”иә«еҲҶйӮ„жҳҜй«”еҲ¶е…§пјҢжҖқжғігҖҒиЁҖи«–еҚ»ж—©е·Іи¶…еҮәй«”еҲ¶вҖ”вҖ”й«”еҲ¶е…§зҡ„жңӢеҸӢеҖ‘дјјд№ҺдёҚж–№дҫҝжҠҠеҺҡжҫӨйӮЈдәӣгҖҺйӣўз¶“еҸӣйҒ“гҖҸзҡ„жҖқжғіеҪҷйӣҶжҲҗеҶҠпјҢе…¬й–ӢеҮәзүҲпјҢд»ҘиҮіж–јеҺҡжҫӨеҺ»дё–иҮід»Ҡдёүе№ҙпјҢжёҜеҸ°пјҲжӣҙйҒ‘и«–дёӯеңӢеӨ§йҷёпјүз«ҹз„ЎдёҖжң¬жңұеҺҡжҫӨжң¬дәәзҡ„ж–ҮйӣҶжҲ–з ”з©¶жңұеҺҡжҫӨзҡ„дҪңе“Ғе•Ҹдё–гҖҚгҖӮйҖҷйғЁгҖҠж–ҮйҒёгҖӢзҡ„еҮәзүҲзөӮж–јеЎ«иЈңдәҶйҖҷдёҖз©әзҷҪгҖӮ
и©Іжӣёз”ұжҶІж”ҝеӯёе®¶ејөеҚҡжЁ№дё»з·ЁпјҢйҖҷдҪҚеүҚдёӯеңӢзӨҫ科йҷўеӯёиҖ…зҸҫеңЁзҫҺеңӢе“ҘеҖ«жҜ”дәһеӨ§еӯёж”ҝжІ»еӯёзі»д»»ж•ҷгҖӮгҖҠж–ҮйҒёгҖӢдҪңзӮәгҖҠдёӯеңӢиҪүеһӢе»әиЁӯж–Үеә«гҖӢзҡ„жңҖж–°дёҖзЁ®жҺЁеҮәпјҢејөеҚҡжЁ№еңЁе°ҺиЁҖдёӯиӘӘпјҡгҖҢеҺҡжҫӨе…Ҳз”ҹеңЁдёӯе…ұй»Ёе…§ж°‘дё»жҙҫиҖҒдәәзҫӨй«”дёӯпјҢжҳҜжҖқжғіе’ҢиӘҚзҹҘеұӨйқўиө°еҫ—жңҖйҒ зҡ„дёҖдҪҚпјҢе°ҚзҸҫеӯҳй«”еҲ¶жңүж·ұеҲ»еҸҚжҖқгҖӮгҖҚ
жңұеҺҡжіҪеҸҜд»Ҙз§°д№Ӣдёәдёӯе…ұзҡ„ејӮзұ»пјҢ1931е№ҙеҮәз”ҹдәҺиҙөе·һз»ҮйҮ‘пјҢ1949е№ҙеҠ е…Ҙдёӯе…ұпјҢжӣҫй•ҝжңҹеңЁиҙөе·һзңҒе·ҘдҪңпјҢ并еңЁ52еІҒж—¶жӢ…д»»иҙөе·һзңҒ委д№Ұи®°пјҢ1985е№ҙ7жңҲи°ғд»»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®Јдј йғЁйғЁй•ҝгҖӮ
1986е№ҙ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еңЁдёӯе®ЈйғЁйғЁй•ҝд»»дёҠжҸҗеҮәдәҶи‘—еҗҚзҡ„вҖңдёүе®Ҫж”ҝзӯ–вҖқ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е®ҪеҺҡгҖҒе®Ҫе®№е’Ңе®ҪжқҫпјҢд»–жң¬дәәд№ҹиў«з§°дёәвҖңдёүе®ҪйғЁй•ҝвҖқгҖӮеҜ№жӯӨ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жӣҫи§ЈйҮҠиҜҙпјҢдёүдёӘвҖңе®ҪвҖқеӯ—пјҢжҸҗеҮәзҡ„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е°ұжҳҜпјҡеҜ№дәҺи·ҹжҲ‘们еҺҹжқҘзҡ„жғіжі•дёҚеӨӘдёҖиҮҙзҡ„жҖқжғіи§ӮзӮ№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йҮҮеҸ–е®Ҫе®№дёҖзӮ№зҡ„жҖҒеәҰпјӣеҜ№еҫ…жңүдёҚеҗҢж„Ҹи§Ғзҡ„еҗҢеҝ—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е®ҪеҺҡдёҖзӮ№пјӣж•ҙдёӘз©әж°”гҖҒзҺҜеўғжҳҜ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жҗһеҫ—е®ҪжқҫгҖҒжңүеј№жҖ§дёҖзӮ№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并没жңүж»Ўи¶ідәҺж”ҝжІ»дёҠдәүеҸ–вҖңдёүе®ҪвҖқпјҢд»–зҡ„жҖқжғіеңЁжҷҡе№ҙж—Ҙи¶ӢжҲҗзҶҹпјҢеҜ№дёӯе…ұзҡ„и®ӨиҜҶжӣҙеҠ ж·ұеҲ»гҖӮжҜ”еҰӮд»–еҜ№вҖң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қзҡ„еү–жһҗе°ұеҫҲзӢ¬еҲ°гҖӮд»–и®ӨдёәвҖң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қдҫқйқ ж”ҝжІ»й«ҳеҺӢпјҢж¶ҲзҒӯдёҖеҲҮдёӘжҖ§е’ҢиҮӘз”ұпјҢз”ЁйӣҶдҪ“зҡ„еҗҚд№үпјҢе®һзҺ°е°‘ж•°дәәеҜ№е…ЁзӨҫдјҡзҡ„жҺ§еҲ¶гҖӮвҖң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қвҖңе°ұжҳҜжҺ§еҲ¶д»–дәәпјӣжүҖи°“йӣҶдҪ“дё»д№үпјҢй“Ғзҡ„зәӘеҫӢпјӣиҜҙеҲ°еә•пјҢе°ұжҳҜд»ҘеӨҡж•°дәәзҡ„еҗҚд№үе®һзҺ°е°‘ж•°дәәзҡ„з»ҹжІ»гҖӮвҖқ
жңұеҺҡжіҪи®ӨдёәвҖң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қеҪўжҲҗдәҺ延е®үж•ҙйЈҺпјҢд»–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иҜӯжғҠеӣӣеә§зҡ„з»“и®әжҳҜпјҡдёӯеҚҺдәәж°‘е…ұе’ҢеӣҪзҡ„жҲҗз«ӢпјҢе°ұжҳҜеҗҜи’ҷиҝҗеҠЁзҡ„з»Ҳз»“гҖӮеӣ дёәвҖң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қд»Һж•ҙдҪ“дёҠж¶ҲзҒӯдәҶдёӘжҖ§е’ҢиҮӘз”ұпјҢжҠҠдёӯеӣҪдәәе…ЁйғҪжҺ§еҲ¶иө·жқҘдәҶгҖӮвҖңеҪ“еҲқпјҢеӨ§е®¶йғҪд»ҘдёәдёҖдёӘж–°зҡ„ж—¶д»ЈеҲ°жқҘдәҶпјҢдёҖдёӘе…Ёж–°зҡ„зӨҫдјҡеҲ°жқҘдәҶпјҢжҚўж–°еӨ©еҳӣпјҢеҢ…жӢ¬жҲ‘们йӮЈдәӣиҖҒдҪң家гҖҒиҖҒ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гҖӮ他们欢呼йӣҖи·ғпјҢй«ҳе…ҙеҫ—дёҚеҫ—дәҶпјҢз»“жһңиҝҪжұӮжқҘзҡ„дёңиҘҝжҳҜдёӘд»Җд№Ҳе‘ўпјҹжҳҜдәүеҸ–ж°‘дё»гҖҒдәүеҸ–иҮӘз”ұгҖҒдәүеҸ–дәәжқғгҖҒдәүеҸ–科еӯҰзҡ„з»“жқҹпјҒ"пјӣвҖңдёҖеҲҮиҮӘз”ұзҡ„гҖҒжңүдёӘжҖ§зҡ„дёңиҘҝйғҪе®ҢдәҶгҖӮвҖқ;вҖңд»ҺиҫӣдәҘйқ©е‘ҪеҲ°д»ҠеӨ©пјҢжҲ‘们иҪ¬дәҶдёҖеңҲпјҢеҸҲиҪ¬еӣһеҲ°дәҶдё“еҲ¶зҡ„иө·зӮ№пјҢиҖҢдё”иҝҷдёӘдё“еҲ¶и¶…иҝҮд»»дҪ•дёҖдёӘжңқд»ЈпјҢе…¶жҺ§еҲ¶зҡ„дёҘй…·еүҚж— еҸӨдәәпјҢе…¶еҜ№жҖқжғізҡ„й’іеҲ¶и¶…иҝҮеҺҶд»ЈпјҢзӣёжҜ”д№ӢдёӢпјҢиҝҮеҺ»йӮЈдәӣж–Үеӯ—зӢұз®—дёҚеҫ—д»Җд№ҲгҖӮвҖқ
жңұеҺҡжіҪеҜ№вҖң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қж·ұжҒ¶з—ӣз»қпјҡвҖңвҖҳе…ҡж–ҮеҢ–вҖҷжҳҜдёӘеҫҲи…җжңҪ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д№ҹжҳҜ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еҺүе®ізҡ„дёңиҘҝгҖӮе®ғж— еӯ”дёҚе…ҘпјҢж— жүҖдёҚеңЁпјҢйқһеёёе •иҗҪпјҢеҚҒеҲҶдё‘жҒ¶гҖӮе®ғиғҪеӨҹеҪўжҲҗеӣӣйқўе…«ж–№зҡ„жё—йҖҸеҠӣйҮҸпјҢиҖҢжҲ‘们иҝҳдёҚеҫ—дёҚе®№еҝҚиҝҷдёӘдёңиҘҝгҖӮжүҖд»Ҙе®ғжҳҜдёҖдёӘж— иҖ»зҡ„ж–ҮеҢ–пјҢз»қж— д»»дҪ•зҫһиҖ»гҖӮдәә们еҜ№иҝҷз§ҚйӮӘжҒ¶дј°и®ЎдёҚи¶іжҳҜдёҚиЎҢзҡ„пјҢиҝҷдәӣдәәеҲ°еӨ„еҶ йқўе ӮзҡҮең°иЎЁжј”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ҚҙеҘҪиҜқиҜҙе°ҪпјҢеқҸдәӢеҒҡз»қгҖӮвҖқ
еҜ№дәҺвҖңзү№иүІ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вҖқе’ҢвҖң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ж°‘дё»вҖқ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з”Ёе…«дёӘеӯ—ж’•дёӢдәҶдјӘиЈ…пјҡвҖңж—ўдёҚвҖҳзӨҫдјҡвҖҷд№ҹдёҚвҖҳж°‘дё»вҖҷгҖӮвҖқе°ұеғҸгҖҠе®үеҫ’з”ҹз«ҘиҜқпјҚзҡҮеёқзҡ„ж–°иЎЈгҖӢйҮҢйӮЈдёӘе°Ҹеӯ©дёҖж ·пјҢжҢҮзқҖе…үеұҒиӮЎзҡҮеёқиҜҙпјҡвҖңд»–д»Җд№Ҳд№ҹжІЎз©ҝе‘ҖпјҒвҖқ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еҗҺжқҘз”Ёжңҙзҙ зӣҙзҺҮзҡ„иҜӯиЁҖпјҢеҜ№иҝҷе…«дёӘеӯ—дҪңдәҶдёҖз•ӘиҜҙжҳҺпјҡд»Җд№ҲеҸ«вҖңж—ўдёҚзӨҫдјҡвҖқе•ҠпјҹжҲ‘们жҳҜд»Ҙ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дҪңдёәзӣ®ж Үзҡ„пјҢжҲ‘们жҳҜж ҮжҰңиҮӘе·ұжҳҜ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иҖ…зҡ„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жҲ‘们иҝҷдёӘе…ҡпјҢеңЁеҸ–еҫ—е…ЁеӣҪж”ҝжқғд»ҘеҗҺпјҢз”ЁеӣҪ家жҠҠзӨҫдјҡвҖңеҗғвҖқжҺүдәҶпјҢвҖңеӣҪ家вҖқжҠҠвҖңзӨҫдјҡвҖқеҗһжІЎдәҶпјҢдёҖеҲҮйғҪеҗ¬е‘ҪдәҺе®ҳж–№пјҢеҗ¬е‘ҪдәҺе®ҳе‘ҳпјҒд»Һе№је„ҝеӣӯз®ЎеҲ°зҒ«и‘¬еңәпјҢд»Һе©ҡ姻зҷ»и®°е°ұејҖе§Ӣз®ЎпјҢиҖҢдё”з®ЎеҲ°зҒ«и‘¬еңәд»ҘеҗҺпјҢдәәе·Із»Ҹжӯ»дәҶпјҢжҲ‘们зҡ„ж”ҝеәңиҝҳиҰҒз®ЎеҲ°д»–пјҲеҘ№пјүзҡ„еӯҗеҘігҖҒд»–пјҲеҘ№пјүзҡ„еҗҺиҫҲгҖӮеңЁи°ҲеҲ°д»–пјҲеҘ№пјүзҡ„еҗҺд»Ј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иҝҳиҰҒзңӢзңӢд»–зҡ„зҘ–е®—гҖҒд»–зҡ„зҲ¶жҜҚжҳҜдёӘд»Җд№ҲдәәпјҢзңҹжҳҜиҚ’е”җд№ӢжһҒгҖӮ
жҖ»д№ӢпјҢеӣҪ家代жӣҝдёҖеҲҮгҖӮд»Җд№ҲеҸ«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пјҹд»ҘзӨҫдјҡдёәдё»д№үпјҢдёәзӨҫдјҡиҖҢдё»д№үпјҢжүҚеҸ«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пјҒжҲ‘们зҡ„зӣ®зҡ„е°ұжҳҜдёәдәҶзӨҫдјҡзҡ„иҝӣжӯҘпјҢдёәдәҶзӨҫдјҡзҡ„з№ҒиҚЈпјҢдёәдәҶзӨҫдјҡзҡ„иҮӘдё»пјҢдёәдәҶзӨҫдјҡз”ҹеҠЁжҙ»жіјең°иҮӘдё»еҗ‘еүҚеҸ‘еұ•гҖӮжҲ‘们еҸҚеҜ№иҝҮеҺ»зҡ„ж”ҝжқғеҜ№зӨҫдјҡзҡ„еҺӢеҲ¶гҖҒз»ҹжІ»гҖҒйҷҗеҲ¶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们жҳҜдёәзӨҫдјҡи§Јж”ҫиҖҢеҘӢж–—зҡ„дёҖзҫӨдәәгҖӮжҲ‘们组жҲҗдёҖдёӘе…ҡпјҢе°ұжҳҜдёҚж»Ўж„ҸеҺҹжқҘйӮЈз§ҚеӣҪ家еҜ№зӨҫдјҡзҡ„з»ҹжІ»гҖҒйҷҗеҲ¶гҖҒдё“еҲ¶пјҒжҳҜдёәдәҶзӨҫдјҡи§Јж”ҫпјҢдёҚдёәдәҶзӨҫдјҡи§Јж”ҫпјҢдҪ жҗһд»Җд№Ҳ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е•Ҡпјҹ
з”Ёж”ҝжқғжҺ§еҲ¶зӨҫдјҡпјҢиҖҢжҠҠзӨҫдјҡиҮӘиә«зҡ„еҸ‘иӮІе’ҢжҲҗй•ҝз»ҷеј„жҺүдәҶгҖӮеңЁз”ЁеӣҪ家жқҘд»ЈжӣҝзӨҫдјҡ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иҝҷдёӘеӣҪ家зҡ„ж”ҝжқғд»Һдә§з”ҹгҖҒжҺҲжқғпјҢдёҖзӣҙеҲ°е®ғзҡ„иҝҗиЎҢиҝҮзЁӢпјҢеҲ°е®ғжқғеҠӣиЎҢдҪҝзҡ„зӣ‘зқЈпјҢжңүжІЎжңүж°‘дё»пјҹжІЎжңүж°‘дё»пјҒжҺҲжқғйғҪдёҚж°‘дё»пјҢжқғеҠӣзҡ„иҝҗиЎҢдёҚжҳҜз”ұж”ҝеәңе’Ңж°‘й—ҙе…ұеҗҢеұҘиЎҢпјҢжқғеҠӣиҝҗиЎҢзҡ„з»“жһңзјәд№ҸжңүеҠӣзҡ„зӣ‘зқЈгҖӮжүҖд»ҘиҜҙжҲ‘们еҪ“д»Ҡзҡ„зӨҫдјҡжҳҜвҖңж—ўдёҚзӨҫдјҡпјҢеҸҲдёҚж°‘дё»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жңұеҺҡжіҪеңЁиІҙе·һеӨ§еӯёжј”и¬ӣиҲҮеё«з”ҹеә§и«ҮжңғдёҠзҡ„и¬ӣи©ұпјҡ
гҖҖгҖҖжқҺе…Ҳз”ҹи®Іеҫ—еҫҲеҘҪгҖӮдёҠеҚҲи®ІпјҢзҺ°еңЁи®ІпјҢе°ұеӨ§е®¶жҸҗеҮәзҡ„иҝҷдәӣй—®йўҳеҸҲеҒҡдәҶдёҖдәӣеҫҲеқҰзҺҮзҡ„дәӨжөҒгҖӮжҲ‘жҳҜйҷӘжқҺе…Ҳз”ҹжқҘзҡ„пјҢжҲ‘дёҖеҶҚиҜҙжҳҺжҲ‘дёҚжҳҜеӯҰиҖ…пјҢжҲ‘жҳҜеҒҡе®һйҷ…е·ҘдҪңзҡ„дәәпјҢиҖҢдё”жҲ‘еҒҡең°ж–№е·ҘдҪңзҡ„ж—¶й—ҙиҫғй•ҝгҖӮжҲ‘и®ІиҝҮпјҢеҒҡең°ж–№е·ҘдҪңжҳҜдҪ“еҠӣеҠіеҠЁпјҢи„‘еҠӣеҠіеҠЁеңЁеҢ—дә¬гҖҒеңЁдёӯеӨ®пјҢе®ҡеӨ§дәӢжғ…пјҢ他们жһ„жҖқеҘҪдәҶпјҢдҪ дёӢйқўе°ұиҙҜеҪ»жү§иЎҢгҖӮ
гҖҖгҖҖеҪ“然пјҢеңЁиҙҜеҪ»жү§иЎҢ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д№ҹжңүдәҶдёҖдәӣж„ҹеҸ—пјҢжүҖд»ҘеҲҡжүҚеҮ дёӘеҗҢеҝ—жҸҗеҲ°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жҲ‘д№ҹиғҪйҒ“еҮәжҲ‘зҡ„дёҖзӮ№ж„ҹеҸ—гҖӮйҰ–е…ҲжҳҜй»Һе…Ҳз”ҹжҸҗеҮә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д»–й—®жҲ‘пјҲдёҠдёӘдё–зәӘпјү80е№ҙд»Јзҡ„вҖңе…«дёӘе®Ҫжқҫе’Ңи°җвҖқжҳҜжҖҺд№ҲжҸҗеҮәжқҘзҡ„пјҹжҲ‘и®°еҫ—жҲ‘们дҪ“ж”№з ”з©¶жүҖеҺҹжқҘжңүдёҖдҪҚеүҜжүҖй•ҝеҸ«еҫҗй”Ұе®үпјҢеҗҺжқҘеҺ»ж·ұеңіеҒҡдҪ“改委主任пјҢд»ҘеҗҺеҸҲдёӢжө·еҚ—еҒҡз”ҹж„ҸеҒҡеҸ‘дәҶгҖӮзҺ°еңЁд»–еӣһиҝҮеӨҙжқҘжңүе…ҙи¶Јз ”з©¶ж–ҮеҢ–й—®йўҳдәҶпјҢдәҺжҳҜе°ұз»ҷжҲ‘еҸ‘дәҶдёҖе°Ғз”өеӯҗйӮ®д»¶пјҢиҝҳзәҰдәҶдёҖдәӣеӯҰиҖ…пјҢдёҺжҲ‘дёҖиө·и®Ёи®әдёӯеӣҪзҡ„ж–°ж–ҮеҢ–е»әи®ҫй—®йўҳгҖӮжҲ‘з®ҖеҚ•ең°еӣһйЎҫдәҶдёҖдёӢжғ…еҶөпјҢжңүдёӘеҸ‘иЁҖпјҢеҗҺжқҘиҝҷдёӘеҸ‘иЁҖз®ҖеҚ•ж•ҙзҗҶдёҖдёӢе°ұеҸ‘еҲ°зҪ‘дёҠеҺ»дәҶпјҢжңүдәӣдәәеҸҜиғҪйғҪе·Із»ҸзңӢи§Ғ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еҲ°дәҶдёӯе®ЈйғЁд»ҘеҗҺпјҢжҲ‘еҚҠе№ҙеӨҡжІЎжңүи®ІиҜқгҖӮеӣ дёәжҲ‘еҺ»д»ҘеүҚпјҢеӨ§жҰӮдёӯеӨ®жңүдёҖдәӣиҖҒеҗҢеҝ—еҜ№ж–ҮйҖүзі»з»ҹдёҚеӨӘж»Ўж„ҸгҖӮжҲ‘и®°еҝҶеҫҲж·ұзҡ„жҳҜдҪң家еҚҸдјҡзҡ„йҖүдёҫпјҢжҗһиҝҷж ·зҡ„йҖүдёҫдҪ е°ұеҫ—жҸҗеүҚдёҖе№ҙж‘ёеә•пјҢжҗһеҗҚеҚ•гҖӮжҚ®иҜҙеҲ°дәҶејҖдјҡеүҚеҗ‘дёӯеӨ®д№Ұи®°еӨ„жұҮжҠҘж—¶пјҢеј е…үе№ҙеҗҢеҝ—е°ұиҜҙиҝҷдёӘеҗҚеҚ•з©¶з«ҹжҳҜжҢҮд»ӨжҖ§зҡ„е‘ўпјҢиҝҳжҳҜжҢҮеҜјжҖ§зҡ„пјҹеҰӮжһңжҳҜжҢҮеҜјжҖ§зҡ„пјҢжҲ‘们е…ҡеҸ¬ејҖе…ҡе‘ҳдҪң家дјҡи®®дҝқиҜҒеҗҚеҚ•йҖүдёҫпјӣеҰӮжһңжҳҜжҢҮеҜјжҖ§зҡ„пјҢжҲ‘们жҠҠиҝҷдёӘж„ҸжҖқз»ҷеӨ§е®¶иҜҙжё…жҘҡпјҢжҸҗдҫӣз»ҷеӨ§е®¶иҖғиҷ‘гҖӮжҲ‘еҪ“ж—¶еңЁиҙөе·һе·ҘдҪңгҖӮеј е…үе№ҙжҸҗеҮә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еҗҺпјҢдј й—»еҪ“ж—¶иғЎиҖҖйӮҰиҜҙпјҡж—ўдёҚжҳҜжҢҮд»ӨжҖ§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жҢҮеҜјжҖ§зҡ„пјҢиҖҢжҳҜж— ж•ҲжҖ§зҡ„гҖӮдҪң家们иҮӘе·ұеҶіе®ҡйҖүи°ҒпјҢе°ұжҳҜи°ҒгҖӮдј иҜҙдёҮйҮҢеҗҢеҝ—еҪ“ж—¶д№ҹеҫҲиөһжҲҗгҖӮжңҖеҗҺйҖүдёҫз»“жһңжҳҜпјҢжҲ‘еӨ§жҰӮжҠҠеҲҳжҹҗйҖүдҪңеүҜдё»еёӯдәҶгҖӮйӮЈжҳҜжңҖжҲҗеҠҹзҡ„дёҖж¬ЎгҖӮжҠҠиҜ—дәәиҙә敬д№Ӣз»ҷйҖүжҺүдәҶпјҢдәә家еҲ°еә•жҳҜ延е®үжқҘзҡ„пјҢеҶҷиҝҮгҖҠзҷҪжҜӣеҘігҖӢгҖӮ
гҖҖгҖҖ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е…¶д»–дәӢпјҢжҲ‘иҝҳдёҚзҹҘйҒ“пјҢеӣ дёәеҪ“ж—¶еңЁиҙөе·һпјҢжҲ‘们满脑иўӢйғҪжҳҜи§ЈеҶіеҗғйҘӯй—®йўҳзҡ„гҖӮеҗҺжқҘжҲ‘иў«и°ғеҲ°дёӯе®ЈйғЁеҺ»дәҶпјҢеҺ»д»ҘеүҚиғЎеҗҜз«ӢеҗҢеҝ—жқҘиҙөе·һпјҢе…¶д»–еҗҢеҝ—д№ҹжқҘдәҶпјҢжҲ‘йғҪжҺҘеҫ…иҝҮ他们гҖӮдҪҶжҲ‘дёҚзҹҘйҒ“д»–жҳҜжқҘе№Ід»Җд№Ҳзҡ„гҖӮе®Ӣд»»з©·д№ҹжқҘиҝҮпјҢиҰҒжҲ‘йҷӘзқҖд»–пјҢд»ҺиҙөйҳіеҲ°йҒөд№үпјҢжҲ‘们еҲ°еӨ„зңӢпјҢдёҖиҫ№зңӢдёҖиҫ№иҒҠпјҢжҲ‘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д»–жқҘе№Ід»Җд№ҲпјҢиҖҒеҗҢеҝ—жқҘе°ұйҷӘдёҖдёӢеҳӣгҖӮиғЎеҗҜз«ӢеңЁиҠұжәӘиҘҝзӨҫеҗғйҘӯпјҢжҲ‘们дёҖиө·ж•ЈжӯҘпјҢйЎәйҒ“еҫҖе№іжЎҘиҝҷдёӘж–№еҗ‘иө°гҖӮ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жқҘзҡ„зӣ®зҡ„жҳҜи·ҹжҲ‘и°ҲдёӯеӨ®и°ғжҲ‘еҺ»дёӯе®ЈйғЁзҡ„дәӢжғ…гҖӮвҖқ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еӨ©дёӢе“ӘжңүиҝҷеӣһдәӢпјҢдҪ з®—з®—дёӯеӣҪе…ұдә§е…ҡеҺҶеұҠе®Јдј йғЁжңүжҲ‘иҝҷз§Қз»ҸеҺҶзҡ„еҗ—пјҹвҖқвҖңжІЎжңүпјҒвҖқд»–иҜҙгҖӮвҖңзҺ°еңЁжҳҜж–°иҖҒеҗҢеҝ—дәӨжӣҝж—¶жңҹпјҢиҖҒеҗҢеҝ—е·Із»ҸиҖҒдәҶгҖӮвҖқ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дәәеӨҡзҡ„жҳҜеҳӣвҖқгҖӮ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е®Јдј йғЁй•ҝиҝҷдёӘиҒҢеҠЎпјҢд»Һй…ҚеӨҮе№ІйғЁи®ІпјҢд№ҹдёҚиғҪе…үжҳҜ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пјҢиҝҳеҫ—жңүең°ж–№е·ҘдҪңз»ҸйӘҢгҖӮвҖқ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йӮЈжңүе•ҠпјҒвҖқжҲ‘еҶ’еҶ’еӨұеӨұзҡ„пјҢжҲ‘иҜҙе№ҝдёңзҡ„д»»д»ІеӨ·еҗҢеҝ—еҫҲжңүз»ҸйӘҢпјҢж°ҙе№іеҸҲйқһеёёй«ҳгҖӮвҖқвҖңд»ІеӨ·еҗҢеҝ—е№ҙзәӘеӨ§дәҶзӮ№пјҢдҪ еҸҲдёҚжҳҜдёҚзҹҘйҒ“гҖӮвҖқвҖңеҪ“然зҹҘйҒ“дәҶпјҢд»ІеӨ·жҜ”жҲ‘еӨ§еҚҒдә”е…ӯеІҒгҖӮвҖқд»–еҸҲй—®пјҡвҖңе№ҙйқ’зҡ„жңүи°ҒпјҹвҖқвҖңйЎ№еҚ—пјҢзҰҸе»әзңҒ委д№Ұи®°гҖӮвҖқжҲ‘жҸҗеҮәдәәйҖүпјҢд»–дёҚиҜҙиҜқдәҶгҖӮжҲ‘дёҚзҹҘйҒ“д»–дёәд»Җд№ҲдёҚиҜҙиҜқпјҹжҲ‘еҺ»дәҶеҢ—дә¬еҮ еӣһпјҢжүҚзҹҘйҒ“еҪ“ж—¶жңүдәәе·Із»Ҹзһ„еҮҶйЎ№еҚ—пјҢиҰҒж•ҙйЎҝд»–дәҶгҖӮдәӢжғ…иө·еӣ дәҺдёҖеҒҮиҚҜдәӢ件гҖӮеҪ“ж—¶жҲ‘ж №жң¬дёҚзҹҘйҒ“иҝҷ件дәӢгҖӮеҶҚеҗҺжқҘжҲ‘еңЁйҫҷеІ©еёӮе·ҘдҪң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дёӢеҺ»еҒҡеҶңжқ‘и°ғжҹҘгҖӮеҶңж°‘и·ҹ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жһ—еҲҷеҫҗзғ§йёҰзүҮпјҢе…ұдә§е…ҡзғ§й“¶иҖізҷҪзі–гҖӮвҖқиҖҒзҷҫ姓еҫҲеҗҢжғ…йЎ№еҚ—гҖӮжүҖд»Ҙи®©жҲ‘дёҠдёӯе®ЈйғЁиҗҪе®һжҢҮеҜјиҝҷ件дәӢжғ…пјҢе°ұжІЎжі•еј„гҖӮйӮЈж—¶еҖҷз§ҳд№Ұй•ҝи®ІпјҢвҖңдҪ иҰҒиө°дәҶпјҢи·ҹзңҒ委зҡ„еҗҢеҝ—дёҖиө·еҗғйҘӯеҗ§пјҹвҖқ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дҪ иҝҳеҗғд»Җд№ҲйҘӯпјҢдҪ дёҚзҹҘйҒ“йӮЈжҳҜи·ізҒ«еқ‘еҳӣ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Ҳ°дәҶеҢ—дә¬д»ҘеҗҺпјҢжҖқжғіи·қзҰ»е°ұжҜ”иҫғеӨ§дәҶгҖӮжҲ‘еҚҠе№ҙжІЎжңүи®ІиҜқпјҢеӣ дёәжҲ‘дё»иҰҒи·ҹеҗ„ж–№йқўеҸӘжҺҘи§ҰпјҢж„ҹи§үзӣёдә’е…ізі»иҝҳжҳҜеҚҒеҲҶзҙ§еј зҡ„гҖӮжҲ‘иҜҙиҝҷиҝҳжҗһд»Җд№Ҳй•ҝжІ»д№…е®үпјҢеҰӮдәәйҷ…е…ізі»йғҪжІЎжҗһеҘҪпјҢдҪ е°ұжІЎеҠһжі•и°ҲиҜқгҖӮдҪ йҰ–е…ҲиҰҒжңүдёӘзӣёдә’дҝЎиө–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еқҗдёӢжқҘеҗҺпјҢдҪ жүҚиғҪи°Ҳй—®йўҳпјҢдёҚ然дҪ д»Җд№Ҳе·ҘдҪңйғҪеҒҡдёҚеҘҪгҖӮжүҖд»ҘдҪ еҲҡжүҚй—®жҲ‘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жҳҜжҖҺд№ҲжҸҗеҮәжқҘзҡ„пјҢд»ҺзӣҙжҺҘж„Ҹд№үдёҠи®Іе°ұжҳҜиҝҷд№ҲжҸҗеҮәжқҘзҡ„гҖӮ
гҖҖгҖҖ1985е№ҙеә•пјҢжңүдёҖж¬ЎиғЎиҖҖйӮҰеҗҢеҝ—й—®жҲ‘пјҢвҖңжҖҺд№Ҳж ·пјҹжқҘдәҶеҘҪеҮ дёӘжңҲпјҢжңүд»Җд№ҲеҸҚжҳ пјҹвҖқ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жҲ‘еҗ¬еҲ°еҸҚжҳ зҡ„е°ұжҳҜдёҖеҸҘиҜқвҖ”вҖ”иҝҷдёӘдәәжқҘдәҶд»ҘеҗҺдёҚи§ҒеҠЁйқҷгҖӮвҖқдёҚжҳҜиҜҙж–°е®ҳдёҠд»»дёүжҠҠзҒ«еҗ—пјҹжҲ‘дёҖжҠҠзҒ«д№ҹжІЎжңүпјҢеҸӘжҳҜз«–иө·иҖіжңөеҗ¬пјҢеҲ°еә•жҖҺд№ҲеӣһдәӢиҝҳжҗһдёҚжё…жҘҡгҖӮеӣһйЎҫдёҖдёӢжҲ‘们е…ҡеңЁеӨ„зҗҶжҖқжғіж–ҮеҢ–й—®йўҳдёҠзЎ®е®һжңүеҫҲеӨҡж•ҷи®ӯ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иҜҙжҳҜдёҚжҳҜе…ҲеҲӣйҖ дёҖдёӘеҸҜд»Ҙзӣёдә’еҜ№иҜқгҖҒзӣёдә’дәӨжөҒзҡ„зҺҜеўғе’Ңж°”ж°ӣгҖӮи·ҜзәҝжҳҜдёӯеӨ®з®Ў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еӨ§ж”ҝж–№й’ҲйғҪжҳҜдёӯеӨ®зӣҙжҺҘз®ЎпјҢжҲ‘们иҝҷдәӣе°ҸдёҚзӮ№еҲӣйҖ зӮ№ж°ӣеӣҙжҖ»еҸҜд»Ҙеҗ§гҖӮжңүзӮ№еҘҪж°ӣеӣҙпјҢе°ұеҸҜд»Ҙдә’зӣёдәӨжҚўж„Ҹи§ҒгҖӮе°ұиҝҷд№ҲдёӘж„ҸжҖқпјҢе°ұжҳҜиҝҷд№ҲзӣҙжҺҘжҸҗеҮәжқҘзҡ„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жҸҗеҮәжқҘд»ҘеҗҺпјҢеҪ“然жңүдёҖдәӣиөһеҗҢзҡ„ж„Ҹи§ҒпјҢд№ҹжңүдёҖдәӣдёҚиөһеҗҢзҡ„ж„Ҹи§ҒпјҢд№ҹжңүдәәеҶҷдҝЎпјҢзҺ°еңЁжүӢйҮҢиҝҳжңүжқҗж–ҷгҖӮжҲ‘жҳҜе…ғжңҲеҲқеҲ°дёҠжө·зҡ„пјҢдёҖеҲ°йӮЈйҮҢпјҢй»„иҸҠе°ұи·ҹд»–еҪ“ж—¶зҡ„дёҖдҪҚе№ҙиҪ»е®Јдј йғЁй•ҝзҺӢиүҜеҢ–пјҢиҝҳжңүжӣҙж—©зҡ„е®Јдј йғЁй•ҝгҖҒеүҜд№Ұи®°пјҢд»ҘеҸҠжҲ‘们иҙөе·һйҒөд№үзҡ„иҖҒд№ЎпјҢдёҖиө·йҷӘжҲ‘дёӢеҺ»зңӢзңӢгҖӮжҲ‘й—®пјҡвҖңдҪ 们иҝҷеҮ еӨ©еңЁе№Ід»Җд№ҲпјҹвҖқ他们иҜҙпјҡвҖңжҳҜеңЁејҖз”өеҪұеҲӣдҪңдјҡгҖӮвҖқжҲ‘иҜҙпјҡвҖңеҘҪдәӢжғ…е•ҠпјҢеҸҜд»ҘеҺ»зңӢзңӢз”өеҪұ家们гҖӮвҖқдёҠжө·жҳҜжҲ‘们дёӯеӣҪз”өеҪұзҡ„еҸ‘жәҗең°пјҢ他们ејҖдәҶдёҖдёӘеҲӣдҪңдјҡпјҢжңүеӨ§жҳҺжҳҹгҖҒеӨ§еҜјжј”гҖҒеӨ§зј–еү§гҖӮ他们иҰҒжҲ‘и®ІиҜқпјҢжҲ‘е°ұи®ІдёҖзӮ№гҖӮеҗҺжқҘжҲ‘еҲ°еӨ©жҙҘпјҢи·ҹдҪң家дёҖиө·ејҖдјҡпјҢеҪ“ж—¶жңүи’ӢеӯҗйҫҷпјҢеҘіеҗҢеҝ—жңүжІҲиӢұгҖӮеҲ°дәҶдёүжңҲд»Ҫе…ЁеӣҪйҹіеҚҸеңЁеҢ—дә¬ејҖдјҡпјҢжҲ‘жҠҠе‘Ёдјҹеҝ—пјҢй«ҳеҗҜзҘҘеҸ«жқҘдәҶпјҢиҝҳеҸ«дәҶзҺ°еңЁзҡ„дёӯеӨ®з»„з»ҮйғЁйғЁй•ҝжқҺжәҗжңқпјҢеҪ“ж—¶д»–жҳҜеӣўдёӯеӨ®д№Ұи®°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дјҡеңәпјҢе°ұеқҗеңЁдёҖиө·еҗғйҘӯпјҢеңЁйӨҗеҺ…иҒҠдәҶдёҖиҒҠпјҢе°ұжҠҠй—®йўҳжҸҗеҮәжқҘпјҢдә’зӣёдәӨжҚўж„Ҹи§ҒгҖӮиҝҷдёӘе°ҸдәӢдёҚд№…е°ұжңүиҖҒеҗҢеҝ—з»ҷдёӯеӨ®еҶҷдҝЎпјҢз»ҷиҖҖйӮҰеҶҷдҝЎгҖӮиҖҖйӮҰжҠҠдҝЎиҪ¬з»ҷжҲ‘пјҢ他们еҜ№е®Ҫжқҫе’Ңи°җзҡ„иҜҙжі•дёҚиөһжҲҗгҖӮиҖҖйӮҰиҜҙпјҡвҖңиҖҒеҗҢеҝ—еҶҷзҡ„дҝЎеҳӣпјҢдҪ з»ҷдәә家з®ҖеҚ•еӣһе°ҒдҝЎд№ҹдёҚеҘҪе•ҠпјҹвҖқжҲ‘иҜҙпјҢвҖңжҲ‘жүҫж—¶й—ҙеҲ°ең°ж–№еҺ»зңӢзңӢ他们еҶҚиҜҙпјҢжүҖд»ҘжІЎжңү马дёҠеӣһдҝЎ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еӣӣжңҲд»ҪпјҢиғЎеҗҜеҠӣеҺ»дәҶдёҖи¶ҹдёҠжө·пјҢй—®йўҳи°Ҳеҫ—еҫҲе№ҝжіӣпјҢ科жҠҖгҖҒз»ҸжөҺгҖҒж–ҮеҢ–йғҪиҜҙдәҶгҖӮзҺ°еңЁдёҠжө·еёӮ委зҡ„дёҖдҪҚеҗҢеҝ—пјҢеҪ“ж—¶еҶҷдәҶдёҖд»Ҫе·ҘдҪңжұҮжҠҘзҡ„и®°еҪ•гҖӮе…¶й—ҙпјҢжҲ‘们еҮҶеӨҮејҖж–ҮеҢ–дјҡпјҢеӯҰд№ дёҖдәӣж–Ү件гҖӮеҗҜз«ӢеӣһеӨҚпјҡе…ідәҺиҝ·дәәд№җйҳҹзҡ„и®ІиҜқпјҢдёҚжҳҜж·ұжҖқзҶҹиҷ‘зҡ„пјҢз”өеҪұиҝҷдәӣдёңиҘҝпјҢз”ұеӨ§е®¶иҜ„и®әгҖӮиҝҷеҸҘиҜқзҡ„иғҢжҷҜ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жҲ‘еҪ“ж—¶иҝҳжҗһдёҚжё…жҘҡгҖӮжңүдёҖж¬ЎпјҢи–„дёҖжіўеҗҢеҝ—пјҢиҝҳжңүйӮ“еҠӣзҘҘ他们еҮ дёӘпјҢжҠҠжҲ‘们еӨ§е®¶дёҖиө·зәҰдәҶеҺ»пјҢе°ұејҖиө·жҺ§иҜүдјҡжқҘпјҢиҜҙиҝҷдёӘз”өеҪұдёҚеә”еҪ“иҜ„йҖүдјҳз§ҖгҖӮи®Іе®Ңд№ӢеҗҺпјҢиҰҒжҲ‘们еӨ§е®¶еҸ‘иЎЁж„Ҹи§ҒгҖӮеҗҜз«ӢеҸ«жҲ‘и®ІпјҢжҲ‘дёҖеҸҘиҜқжІЎи®ІпјҢжҗһдёҚжё…жҘҡжҖҺд№Ҳи®ІгҖӮеҗҜз«Ӣи®ІдәҶдёҖз•ӘиҜқпјҢеҗҺжқҘе°ұжҠҠиҝҷдәӣдёңиҘҝж•ҙзҗҶеҸ‘иЎЁеҮәеҺ»пјҢе…¶дёӯе°ұжҸҗеҲ°еҗҜз«Ӣе…ідәҺиҝ·дәәд№җйҳҹзҡ„и®ІиҜқ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д»–иҜҙйӮЈдёӘи®ІиҜқдёҚжҳҜж·ұжҖқзҶҹиҷ‘зҡ„гҖӮеҗҜз«ӢжҺҘзқҖи®ІдәҶжҲ‘еңЁдёҠжө·и®Ізҡ„дёҖз•ӘиҜқгҖӮжҲ‘иҝҷдёӘдәәи®ІиҜқдёҚз”ЁзЁҝеӯҗпјҢж„ҝж„ҸдәӨжҚўж„Ҹи§ҒпјҢеҸҚжӯЈжҲ‘们иҜҙиҜқдёҚдҪңж•°гҖӮжҳҜдёҚжҳҜжңүдәәй—®еҲ°жңұеҺҡжіҪеҮәжқҘзҡ„и®ІиҜқпјҢиҝҳжңүд»–и®Ізҡ„иҝҷдёӘе®Ҫжқҫе’Ңи°җи·ҹдёӯеӨ®жұҮжҠҘиҝҮжІЎжңүгҖӮеӣ дёәжІЎжңүи®°еҪ•пјҢжҳҜжҲ‘зҢңзҡ„гҖӮеҗҺжқҘжҲ‘зңӢдёҠжө·еҸ‘иЎЁгҖҠеҗҜеҠӣеҗҢеҝ—еҲ°дёҠжө·и§ҶеҜҹзҡ„и®ІиҜқгҖӢпјҢд»–е°ұжҸҗеҲ°еӣўз»“гҖҒе’Ңи°җгҖҒзӣёдә’зҗҶи§ЈгҖҒзӣёдә’дҝЎиө–гҖӮеҗҜеҠӣиҜқеҮәжқҘд»ҘеҗҺпјҢгҖҠж–ҮиүәжҠҘгҖӢдҫҝжҠҠжҲ‘еҜ№йҹіеҚҸи®Ізҡ„иҜқд№ҹеҸ‘еҮәеҺ»пјҢе…¶д»–жҠҘзәёжүҚејҖе§ӢиҪ¬иҪҪгҖӮжҲ‘并没жңүиҰҒжұӮ他们иҪ¬иҪҪгҖӮж–°еҚҺзӨҫеҸ‘зҡ„еҶ…е®№пјҢжҲ‘иҜҙе…ідәҺжҲ‘иҜҙеҮәеҺ»зҡ„иҜқпјҢйғҪдәӨз»ҷжҲ‘ж”ҫеңЁжҠҪеұүйҮҢпјҢдёҖдёӘжІЎжӢҝеҮәеҺ»пјҢеҗҺжқҘеҗ„ж–№йқўи®®и®әеҫҲеӨҡпјҢжҲ‘д№ҹеңЁз»§з»ӯи®ІгҖӮ
гҖҖгҖҖе…ідәҺвҖңдёүдёӘе®ҪжқҫвҖқпјҢиҝҷйҮҢд№ҹз•ҘеҠ д»Ӣз»ҚгҖӮж–ҮеҢ–йғЁејҖе…ЁеӣҪж–ҮеҢ–еҺ…еұҖй•ҝдјҡи®®пјҢз”ұй«ҳеҚ зҘҘдё»жҢҒгҖӮжҲ‘дёҠеҚҲеҗ¬е®Ңдјҡи®®еҗҺпјҢдёӢеҚҲе°ұеҺ»е…«е®қеұұеҸӮеҠ дёҖдёӘиҖҒеҗҢеҝ—зҡ„йҒ—дҪ“е‘ҠеҲ«д»ӘејҸгҖӮ然еҗҺжүҚеӣһеҲ°дјҡеңәгҖӮдёҖеҲ°дјҡеңәпјҢй«ҳеҚ зҘҘе°ұиҰҒжҲ‘еҸ‘иЁҖгҖӮжҲ‘иҜҙжҲ‘жҳҜжқҘеҗ¬еӨ§е®¶еҸ‘иЁҖзҡ„гҖӮвҖңдёҠеҚҲе·Із»ҸејҖе®ҢдјҡдәҶпјҢжҲ‘жІЎе‘ҠиҜүдҪ пјҢдҪ жқҘи®ІеҳӣгҖӮвҖқй«ҳеҚ зҘҘиҜҙгҖӮе°ұиҝҷж ·пјҢжҲ‘и®ІдәҶе…ідәҺж–ҮеҢ–й—®йўҳзҡ„еҮ зӮ№жҖқиҖғгҖӮеҗҺжқҘгҖҠзәўж——гҖӢжқӮеҝ—е°ұејҖе§Ӣжү№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зҺ°еңЁпјҢжҲ‘з»ҷдҪ 们讲дёҖдёӘе°Ҹж•…дәӢгҖӮжҲ‘们йӮЈдёӘ马еҲ—жүҖжүҖй•ҝиӢҸе°‘еҝ—жҳҜдёӘиҖҒеӨ«еӯҗпјҢд»–и®ІдәҶдёҖдёӘе®Ҫжқҫе’Ңи°җгҖӮгҖҠзәўж——гҖӢжқӮеҝ—жҠҠд»–зҡ„иҜқж”№жҲҗвҖңеӣўз»“е’Ңи°җвҖқгҖӮиӢҸеӨ«еӯҗеҫҲи®Ўиҫғиҝҷ件дәӢпјҢеҝғжғіжҖҺд№Ҳж”№дәҶдёҚз»ҷжҲ‘иҜҙе‘ўпјҹдәҺжҳҜд»–е°ұеҶҷдәҶдёҖе°ҒдҝЎз»ҷдәҺе…үиҝңгҖӮеҪ“ж—¶дәҺе…үиҝңжҳҜ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зҡ„еүҜйҷўй•ҝгҖӮе…үиҝңеҗҢеҝ—иҷҪ然еҫҲеҝҷпјҢдҪҶд»–еҜ№йӮЈе°ҒдҝЎеҫҲйҮҚи§ҶпјҢд»–жҠҠеҺҹдҝЎе’Ңд»–зҡ„еӣһдҝЎеҜ„з»ҷеҗҜеҠӣеҗҢеҝ—е’ҢжҲ‘гҖӮдёәиҝҷ件дәӢпјҢе…үиҝңеҗҢеҝ—жҢҮеҮәжҲ‘д»¬е®Јдј жңүжҜӣз—…пјҢд»Җд№ҲйғҪиҰҒеҜ№еҸЈеҫ„пјҢд»ЈиЎЁеӨ§дјҡжҠҘе‘Ҡз”ЁиҜҚиҰҒжҺЁж•ІпјҢдёӘдәәи®ІиҜқеҳӣпјҢз®—д»Җд№Ҳпјҹз”ҹеҠЁжҙ»жіјеҳӣ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д»–еҸҲеҶҷдәҶдёҖе°ҒдҝЎз»ҷеҗҜеҠӣе’ҢжҲ‘гҖӮиҝҷдёӘдҝЎиҝҳеңЁжҲ‘йӮЈе„ҝгҖӮеүҚж®өж—¶й—ҙзҝ»дёңиҘҝ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еҸҲжҠҠиҝҷе°ҒеҮ еҚҒе№ҙеүҚзҡ„дҝЎзңӢдәҶдёҖйҒҚпјҢжҲ‘зңӢеҫ—笑дәҶиө·жқҘгҖӮдәҢеҚҒеҮ е№ҙеҗҺзҡ„д»ҠеӨ©пјҢвҖңе’Ңи°җвҖқиҝҷдёӘиҜҚеңЁжҲ‘д»¬дј еӘ’дёҠдҪҝз”Ёйў‘зҺҮеҫҲй«ҳе•ҠгҖӮ
гҖҖгҖҖиҮідәҺжҲ‘зҡ„ж„ҹжғіпјҢдёҖеҲҷе–ңпјҢдёҖеҲҷеҝ§пјҢдёҖеҲҷжғ§гҖӮе–ңеҳӣпјҢз»•дәҶдёҖдёӘеҫҲеӨ§зҡ„еңҲеӯҗпјҢзҺ°еңЁеӨ§е®¶йғҪиөһжҲҗе’Ңи°җгҖӮеҝ§д»Җд№Ҳпјҹе°ұжҳҜжҲ‘们е’Ңи°җеҰӮдҪ•зҗҶи§ЈдёҺе’Ңи°җеҰӮдҪ•е®һзҺ°гҖӮжғ§д»Җд№ҲпјҹжҲ‘еҫҲжӢ…еҝғдёҖдәӣиў«еӨ§е®¶иөһжҲҗзҡ„жҷ®дё–жҖ§жҰӮеҝөпјҢеҲ°дёҖдәӣең°ж–№дјҡеҸҳеҪўпјҢжңҖеҗҺдёҚзҹҘйҒ“дјҡеҸҳжҲҗд»Җд№ҲдёңиҘҝгҖӮе’Ңи°җиҝҷдёӘиҜҚдёҚжҳҜжҲ‘еҲӣйҖ зҡ„гҖӮжҲ‘зҡ„ж„ҹжғіж— йқһе°ұжҳҜеҲҡжүҚи®Ізҡ„пјҢжҲ‘们еёҢжңӣжңүдёҖдёӘеҘҪзҡ„ж°ӣеӣҙпјҢе’Ңи°җжҳҜжҲ‘们еӨ§е®¶зҡ„зҗҶжғіпјҢд№ҹжҳҜжҲ‘们许еӨҡдәәзҡ„иҝҪжұӮ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е»әи®®жўізҗҶдёҖдёӢ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зҡ„еҺҶеҸІгҖӮжҢүз…§жҲ‘еӨ§дҪ“зҡ„еҚ°иұЎпјҢ第дёҖж¬Ўејәи°ғзү№иүІжҳҜеңЁж–ҜеӨ§жһ—еҺ»дё–д»ҘеҗҺ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иӢҸе…ұдәҢеҚҒеӨ§д»ҘеҗҺпјҢй’ҲеҜ№д»–们жҡҙйңІеҮәжқҘ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жҜӣдё»еёӯе°ұе·Із»ҸеңЁиҖғиҷ‘дёӯеӣҪе»әи®ҫиҰҒеҗёеҸ–иӢҸиҒ”зҡ„з»ҸйӘҢе’Ңж•ҷи®ӯгҖӮжҜӣдё»еёӯйҰ–е…ҲиҖғиҷ‘зҡ„й—®йўҳеӨ§жҰӮе°ұжҳҜвҖңеҚҒеӨ§е…ізі»вҖқпјҢе°ұжҳҜдёӯеӣҪзҡ„е»әи®ҫиҰҒжңүдёҖзӮ№иҮӘе·ұзҡ„зү№зӮ№гҖӮд»–жүҖи®Ізҡ„зү№зӮ№жҳҜй’ҲеҜ№иӢҸиҒ”жЁЎејҸзҡ„гҖӮд»ҺеӨ§и·ғиҝӣгҖҒдәәж°‘е…¬зӨҫпјҢеҲ°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пјҢи®Ізҡ„е°ұжҳҜиҝҷдёӘгҖӮ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е№ҙе№ҙи®ІгҖҒжңҲжңҲи®ІгҖӮз ”з©¶иҝҷж®өеҺҶеҸІпјҢжҲ‘们еҸ‘зҺ°еҪ“ж—¶жҳҜдёҖдёӘеҫҲеӨ§зҡ„иҪ¬еҸҳгҖӮе°ұеҺҶеҸІз»ҸйӘҢиҖҢиЁҖпјҢж–ҜеӨ§жһ—жӣҫз»ҸжҺЁиЎҢжһҒе·Ұзҡ„ж— дә§йҳ¶зә§дё“ж”ҝпјҢеҜ№дәҺе…¶жүҖиЎЁзҺ°еҮәжқҘзҡ„ж®ӢжҡҙжҖ§зҡ„дёҖйқўпјҢжҲ‘们жҳҜжү№иҜ„зҡ„гҖӮ然иҖҢеҲ°дәҶ1962е№ҙпјҢз»ҸжөҺи°ғж•ҙд»ҘеҗҺпјҢеҢ—жҲҙжІідјҡи®®еҚҙејәи°ғ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иҰҒеӨ©еӨ©и®ІгҖҒжңҲжңҲи®ІгҖҒе№ҙе№ҙи®ІгҖӮе®Ңе…Ёзҝ»дәҶиҝҮжқҘгҖӮеҗҺжқҘзҡ„вҖңж–ҮеҢ–еӨ§йқ©е‘ҪвҖқжӣҙжҳҜзӘҒеҮәгҖӮ
гҖҖгҖҖ第дәҢж¬Ўејәи°ғзү№иүІжҳҜеңЁвҖңж–ҮеҢ–еӨ§йқ©е‘ҪвҖқз»“жқҹд»ҘеҗҺгҖӮеҪ“ж—¶пјҢе°Ҹе№іеҗҢеҝ—е·Із»ҸжҒўеӨҚж—Ҙеёёе·ҘдҪңгҖӮд»–и®ӨиҜҶеҲ°дёӯеӣҪдёҚиғҪеҶҚеғҸвҖңж–ҮеҢ–еӨ§йқ©е‘ҪвҖқйӮЈж ·з»§з»ӯдёӢеҺ»дәҶпјҢиҝҷдёҖзӮ№жҳҜжңүе…ұиҜҶзҡ„гҖӮдҪҶжҳҜдёӯеӣҪиҜҘеҰӮдҪ•иө°дёӢеҺ»пјҢд»Қ然зјәе°‘е…ұиҜҶгҖӮй’ҲеҜ№жҜӣдё»еёӯжҗһдәҶеҚҒеҮ е№ҙзҡ„жЁЎејҸпјҢе°Ҹе№іеҗҢеҝ—жҸҗеҮәдёҖдёӘ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зҡ„жЁЎејҸгҖӮд»–иҜҙжҲ‘们иҰҒ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ҢиҰҒжңүдёҖзӮ№ж–°зҡ„дёңиҘҝгҖӮдҪҶжҳҜиҝҷж¶үеҸҠдёӨж–№йқўпјҡ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еқҡжҢҒ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пјӣеҸҰдёҖйқўеҫ—и®І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гҖӮз ”з©¶еҺҶеҸІзҡ„еҗҢеҝ—пјҢеҸҜд»Ҙж…ўж…ўең°жҸЈж‘©жё…жҘҡгҖӮ
гҖҖгҖҖиҝ‘дәӣе№ҙпјҢжҲ‘们еҶҚж¬Ўејәи°ғ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еӨ§жҰӮе°ұжҳҜеҮ е№ҙеүҚ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и°ўйҹ¬еҸ‘иЎЁгҖҠеҸӘжңүж°‘дё»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жүҚиғҪж•‘дёӯеӣҪгҖӢдёҖж–ҮгҖӮиҜҘж–Үе®һйҷ…дёҠжҳҜз»ҷиҫӣеӯҗйҷөзҡ„гҖҠеҚғз§ӢеҠҹзҪӘжҜӣжіҪдёңгҖӢдёҖд№ҰжүҖж’°зҡ„еәҸиЁҖпјҢеҗҺжқҘж”№дәҶдёҖдёӘйўҳзӣ®зҷ»еңЁгҖҠзӮҺй»„жҳҘз§ӢгҖӢдёҠпјҢж–°йўҳдёәгҖҠж°‘дё»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дёҺдёӯеӣҪеүҚйҖ”гҖӢпјҢеҺҹеӣ еҺҹжқҘзҡ„еҗҚеӯ—еӨӘеҲәжҝҖдәҶпјҒеҺҹж–°й—»еҮәзүҲзҪІзҪІй•ҝжҳҜжҗһж–°й—»зҡ„пјҢйўҳзӣ®жҳҜд»–ж”№зҡ„гҖӮж–Үз« еҸ‘еҮәеҺ»д»ҘеҗҺпјҢеј•иө·дәҶе№ҝжіӣзҡ„и®Ёи®әпјҢиөһжҲҗиҖ…жңүд№ӢпјҢеҸҚеҜ№иҖ…жңүд№ӢгҖӮйӮЈдәӣжңүзқҖдә”е…ӯеҚҒе№ҙе…ҡйҫ„зҡ„иҖҒеҗҢеҝ—з»ҲдәҺжҳҺзҷҪдәҶиҝҷжҳҜжҖҺд№ҲеӣһдәӢпјҢеӣ дёәд»–еңЁж–Үз« дёӯжўізҗҶдәҶжҒ©ж јж–ҜеҗҺжңҹзҡ„жҖқжғіпјҢжҲ‘们дёҖдәӣиҖҒеҗҢеҝ—жІЎжңүиҜ»иҝҮиҝҷдәӣдёңиҘҝпјҢгҖҠе…ұдә§е…ҡе®ЈиЁҖгҖӢиҜ»дәҶпјҢдҪҶжҳҜдёӨзҜҮеәҸиЁҖжІЎжңүиҜ»пјҢеӣ жӯӨжүҖи°“и®І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е°ұжңүй—®йўҳ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з”ұдәҺдәүи®әжҝҖзғҲпјҢ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жңә关并жңӘйҮҮеҸ–жһӘжҜҷзҡ„еҠһжі•пјҢж—ўжІЎжңүи®©гҖҠзӮҺй»„жҳҘз§ӢгҖӢе…ій—ӯ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и®©и°ўйҹ¬еҒҡжЈҖи®ЁпјҢж—ўдёҚжү№иҜ„пјҢд№ҹдёҚиөһжү¬гҖӮе…¶е®һдёӯеӣҪзӨҫ科йҷўжҳҜеёҰеӨҙжү№иҜ„пјҢеҪ“ж—¶дёҠжө·зӨҫ科йҷўе’ҢжөҷжұҹзӨҫ科йҷўйғҪеңЁеҳӣпјҒз ”з©¶еҪ“д»ЈдёӯеӣҪжҖқжғіеҸІзҡ„дәәйғҪзҹҘйҒ“пјҢеҗҺжқҘгҖҠдәәж°‘ж—ҘжҠҘгҖӢд»Ҙзӯ”иҜ»иҖ…й—®зҡ„еҪўејҸеҒҡдәҶдёҖдёӘз®Җзҹӯзҡ„еӣһзӯ”пјҢжҳҺзЎ®ең°жӢ’з»қдәҶи°ўйҹ¬зҡ„ж–Үз« ж Үйўҳ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们еқҡжҢҒиө°дёӯеӣҪзү№иүІзҡ„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йҒ“и·ҜгҖӮдҪ 们жҳҜз ”з©¶жҖқжғігҖҒж–ҮеҢ–й—®йўҳзҡ„пјҢдҪ 们и·ҹжҲ‘们дёҚеҗҢпјҢжҲ‘们иҝҷдәӣиҖҒеӨҙжҳҜдәӣй—ІдәәпјҒжүҖд»ҘеҸӘжҳҜ马иҷҺ马иҷҺең°иҜҙиҜҙиҖҢе·ІгҖӮдҪ 们еә”иҜҘжҠҠе®ғжўізҗҶдёҖдёӢгҖӮй—®йўҳйҰ–е…ҲдёҚжҳҜеӯҰжңҜжҖ§е‘ҪйўҳпјҢиҖҢжҳҜж”ҝжІ»жҖ§е‘ҪйўҳгҖӮдҪ 们иҰҒзҹҘйҒ“ж”ҝжІ»жҖ§е‘ҪйўҳжҳҜй’ҲеҜ№д»Җд№Ҳи®Ізҡ„пјҢ然еҗҺжүҚиғҪеј„жё…жҘҡе®ғ究з«ҹиҜҙзҡ„жҳҜд»Җд№ҲпјҢдёҚ然дҪ 们жҗһдёҚжё…жҘҡгҖӮе…ідәҺи°ўйҹ¬зҡ„ж–Үз« пјҢдҪ 们еңЁзҪ‘дёҠжҹҘдёҚеҲ°жҲ‘зҡ„и°ҲиҜқе’ҢеҸ‘иЁҖпјҢдҪҶе®һйҷ…дёҠжҲ‘们议и®әиҝҮеҫҲеӨҡж¬ЎпјҢеҸӘжҳҜжІЎжңүеҶҷжҲҗж–Үз« гҖӮи°ўйҹ¬зҡ„ж–Үз« еҪ“然з»ҷжҲ‘и®ёеӨҡеҗҜеҸ‘пјҢдҪҶжҲ‘дёҚе®Ңе…ЁиөһеҗҢпјҢ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дёҖдёӘеҪұе“ҚеҫҲеӨ§зҡ„жҖқжғіе®¶пјҢд»–зҡ„еӯҰжңҜпјҢжҖқжғіи§ӮзӮ№пјҢеңЁеҗ‘еүҚдј йҖ’е’ҢеҸ‘еұ•зҡ„иҝҮзЁӢеҪ“дёӯжҳҜдёҖе®ҡиҰҒеҲҶиЈӮзҡ„пјҢд»–дёҖе®ҡдјҡеҲҶеҢ–дёәиӢҘе№ІдёӘжҙҫеҲ«пјҢиҝҷдәӣдёҚеҗҢзҡ„жҙҫеҲ«пјҢиҰҒиҜҒжҳҺе“ӘдёӘжҳҜжӯЈз»ҹпјҢе“ӘдёӘжҳҜдҝ®жӯЈгҖӮжҲ‘еҜ№иҝҷдёҖзңӢжі•е°ұдёҚеӨӘиөһеҗҢгҖӮжҜ”еҰӮиҜҙпјҢеҲ—е®Ғе°ұ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е®Ңе…Ёзҡ„ж”ҝ治家гҖӮд»–жҳҜдёҖдёӘеӯҰиҖ…пјҢжңүеӨ§йҮҸзҡ„иҜ»д№Ұ笔记гҖӮд»ҺеҲ—е®Ғзҡ„иҜ»д№Ұ笔记жқҘзңӢпјҢд»–жүҖиҜ»зҡ„д№ҰдёҚе®Ңе…ЁжҳҜеҪ“ж—¶жңҖжңүеҗҚзҡ„дәәеҶҷзҡ„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еҗҰжңүеҗҚпјҢеҲ—е®ҒйғҪдјҡеңЁд»–жүҖиҜ»зҡ„д№ҰдёҠеҲ’еңҲпјҢ并еҶҷдёӢиӢҘе№Іжү№иҜӯгҖӮжүҖд»ҘеҲ—е®Ғзҡ„д»»дҪ•и§ӮзӮ№пјҢжҜҸдёӘдәәжҠ“еҲ°дёҖзӮ№йғҪеҸҜд»ҘеҸ‘еұ•еҮәдёҖдёӘжҙҫеҲ«пјҢиҖҢд»–жүҖжҸҗеҮәзҡ„й—®йўҳйғҪеҸҜд»Ҙи®Ёи®ә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жңүдёҖзҜҮжІЎжңүеҸ‘иЎЁзҡ„ж–Үз« йўҳзӣ®жҳҜпјҡе…Ёйқўж”№йқ©зҡ„е®ЈиЁҖд№Ұ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е®ЈиЁҖд№Ұдёӯ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иҜҙпјҡвҖңдёӯеӣҪзҡ„ж”№йқ©иө°еҲ°д»ҠеӨ©пјҢеӣ°йҡҫйҮҚйҮҚпјҢй—®йўҳзҡ„ж №жң¬еңЁдәҺж”№йқ©и¶ҠжқҘи¶Ҡиө°еҗ‘зүҮйқў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”ҝжІ»ж”№йқ©жІЎжңүи·ҹдёҠз»ҸжөҺж”№йқ©зҡ„жӯҘдјҗгҖӮ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зҡ„еҸ‘еұ•йңҖиҰҒеҒҘе…Ёзҡ„ж°‘дё»жі•жІ»зҡ„еҲ¶еәҰзҺҜеўғпјҢдҪҶжҳҜпјҢдёӯеӣҪзҡ„ж”ҝжІ»ж°‘дё»еҢ–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еҫ—еҲ°ж №жң¬зҡ„иҝӣжӯҘ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иҜҙпјҢиғЎиҖҖйӮҰдё»еј зҡ„ж”№йқ©жҳҜе…Ёйқўзҡ„ж”№йқ©гҖӮиғЎиҖҖйӮҰеңЁ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е·ҘдҪңдёҠжҳҜејҖж”ҫзІҫзҘһгҖӮжңұеҺҡжіҪиҜҙпјҢе…ідәҺеӨ„зҗҶе…ҡеҶ…дёӨз§ҚдёҚеҗҢзҹӣзӣҫзҡ„жҖқжғіпјҢжӯЈжҳҜиғЎиҖҖйӮҰиҮӘе·ұйҰ–е…ҲжҸҗеҮәвҖқеӣӣдёҚвҖң(дёҚжҠ“иҫ«еӯҗгҖҒдёҚжҲҙеёҪеӯҗгҖҒдёҚжү“жЈҚеӯҗгҖҒдёҚиЈ…иўӢеӯҗ(жЎЈжЎҲ))зҡ„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еј•з”ЁиғЎиҖҖйӮҰзҡ„иҜқиҜҙпјҡжҜӣжіҪдёңеҗҢеҝ—жҷҡе№ҙжҒ°жҒ°дёҚе–„дәҺеӨ„зҗҶе…ҡеҶ…иҝҷз§ҚиҢғеӣҙзҡ„зҹӣзӣҫпјҢз»“жһңе°ұйҖ жҲҗдёҖз§ҚйЈҺж°”пјҡдёҚдҪҶеҗ¬дёҚеҫ—дёҚеҗҢж„Ҹи§ҒпјҢиҖҢдё”жҠҠдёҚиөһжҲҗе’ҢдёҚе®Ңе…ЁиөһжҲҗиҮӘе·ұдё»еј зҡ„еҘҪж„Ҹи§ҒпјҢеҪ“жҲҗвҖңеҸіеҖҫвҖқгҖҒвҖңиө°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йҒ“и·ҜвҖқгҖҒвҖңеҸҚе…ҡвҖқ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й—ҙжҺҘеҗ«и“„жү№еҲӨдәҶдёӯе…ұжңҖй«ҳйўҶеҜјеұӮгҖӮ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дёҚе…Ғи®ёжҠҠдёҚеҗҢж„Ҹи§ҒеҪ“дҪңеҸҜд»Ҙи®Ёи®әдәүи®ә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дёҚе…Ғи®ёеңЁе№ізӯүзҡ„ж„Ҹд№үдёҠеҺ»жҺўи®ЁпјҢе·Із»ҸйҖ жҲҗдәҶжһҒе…¶дёҘйҮҚзҡ„еҗҺжһңпјҢйӮЈе°ұжҳҜи°ҒжҺҢжқғи°Ғе°ұжҳҜеӨ©з»Ҹең°д№үең°зҷҫеҲҶд№ӢзҷҫжӯЈзЎ®пјҢйҡҸдҫҝиҜҙдёӘд»Җд№ҲиҜқпјҢд№ҹе°ұеҸҳжҲҗ马е…ӢжҖқдё»д№үзҡ„ж–°еҸ‘еұ•пјҢйғҪиҰҒжҺҘдёҠйӮЈдёӘжүҖи°“зҡ„вҖң马е…ӢжҖқдё»д№үдёӯеӣҪеҢ–вҖқзҡ„и°ұзі»гҖӮдҪ зңӢжҲ‘们е…ҡзҡ„з« зЁӢдёҠзҪ—еҲ—дәҶеӨҡе°‘еҗҚеӯ—пјҹеғҸдёҚеғҸеҸ зҪ—жұүзҡ„жёёжҲҸпјҹиҚ’е”җеҳӣпјҒиҝҷе°ұйҳ»зўҚдәҶзңҹжӯЈзҡ„зҗҶи®әиҝӣжӯҘпјҢеӣ дёәиҝҷзӯүдәҺжҳҜиҜҙжңҖй«ҳзңҹзҗҶзҡ„еҸ‘жҳҺжқғе’Ңи§ЈйҮҠжқғж°ёиҝңеңЁжңҖй«ҳеҪ“жқғиҖ…жүӢйҮҢгҖӮеҸӘиҰҒжңүдёҚеҗҢж„Ҹи§ҒпјҢжҲ–иҖ…жғіеңЁ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дёҠиҝӣиЎҢжҺўи®ЁпјҢе°ұеҸҳжҲҗдәҶвҖңеҸҚвҖқзҡ„дёҖйқў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з»“жһңеӨҡеҸҜжҖ•пјҹпјҒ
*дәәиҖҒеҝғдёҚиҖҒ зҪ‘еҗҚZHZ*
жңұеҺҡжіҪдәәиҖҒеҝғдёҚиҖҒгҖӮдәәеҲ°жҷҡе№ҙпјҢж— е®ҳдёҖиә«иҪ»гҖӮж–°дә¬жҠҘиҜҙпјҢд»–жӣҫеҜ№еҘіе„ҝжңұзҺ«иҜҙпјҢжғід№°дёҖиҫҶе°ҸжҺ’йҮҸзҡ„QQжұҪиҪҰпјҢеҸҜеӯ©еӯҗ们и§үеҫ—дёҖдёӘй«ҳе®ҳд№°иҝҷиҪҰеҫҲдёўйқўеӯҗ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дёҚд»Ҙдёә然пјҡдёҚе°ұжҳҜд»ЈжӯҘе·Ҙе…·еҗ—пјҢжҲ‘е°ұеңЁдёҮеҜҝи·ҜжӢүзқҖдҪ еҰҲд№°иҸңгҖӮ
жңұеҺҡжіҪжҙ»еҲ°иҖҒеӯҰеҲ°иҖҒгҖӮ2005е№ҙ11жңҲпјҢ75еІҒзҡ„жңұеҺҡжіҪеңЁж–°жөӘзҪ‘ејҖдәҶеҚҡе®ўпјҢйқһеёёдҪҺи°ғпјҢеҸ–дёҖдёӘзҪ‘еҗҚжҳҜZHZгҖӮ
еңЁзҫҺеӣҪе®ҫеӨ•жі•е°јдәҡе·һзәҰе…ӢеӯҰйҷўж•ҷд№Ұзҡ„еҺҶеҸІеӯҰиҖ…е‘ЁжіҪжө©иҜҙпјҢд»Һдёӯе…ұжү§ж”ҝд»ҘжқҘпјҢдёӯе®ЈйғЁе°ұдёҖзӣҙеҗҚеЈ°дёҚдҪігҖӮзәҰе…ӢеӯҰйҷўж–°й—»зҪ‘жҸҙеј•е‘Ёж•ҷжҺҲзҡ„иҜқиҜҙпјҢдҪҶжңұеҺҡжіҪеҸҠе…¶еүҚд»»йӮ“еҠӣзҫӨзҡ„еҒҡжі•еҲҷе®Ңе…ЁдёҚеҗҢгҖӮе‘ЁжіҪжө©иҜҙ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е®һиЎҢзҡ„жҳҜдёүе®ҪпјҢд»–дё»ж”ҝдёӯе®ЈйғЁйӮЈдёӘйҳ¶ж®өпјҢжҳҜдёӯе®ЈйғЁеҺҶжқҘжңҖй—Әе…үзҡ„ж—¶жңҹгҖӮ
*жң¬жҳҜжҖ»д№Ұи®°дәәйҖүпјҹ*
жӣҫжҙҫй©»еҢ—дә¬еӨҡе№ҙзҡ„зәҪзәҰж—¶жҠҘи®°иҖ…зәӘжҖқйҒ“(Nick Kristof )5жңҲ19еҸ·еңЁд»–зҡ„жҺЁзү№дёҠиҜҙ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жҳҜдёӯеӣҪдәҶдёҚиө·зҡ„ж”№йқ©жҙҫдәәеЈ«пјҢ1989е№ҙ(ж°‘иҝҗиў«)й•ҮеҺӢеҗҺпјҢд»–д№ҹйҒӯеҲ°ж•ҙиӮғгҖӮжң¬жқҘд»–жҳҜиҰҒеҪ“дёӯе…ұжҖ»д№Ұи®°зҡ„гҖӮ
жңүе…іжңұеҺҡжіҪиҰҒеҪ“дёӯе…ұжҖ»д№Ұи®°зҡ„иҜҙжі•пјҢиҝҳи§ҒиҜёдёҖдәӣж–Үз« гҖӮжҜ”еҰӮпјҢй«ҳз‘ңеңЁжңҖж–°еҸ‘иЎЁзҡ„зәӘеҝөжңұеҺҡжіҪж–Үз« дёӯеј•з”ЁеӯҰиҖ…дёҒдёңзҡ„иҜқиҜҙпјҡиғЎиҖҖйӮҰз”ҹеүҚжңҖеҗҺзҡ„и®ІиҜқдёӯиҜҙпјҡжҲ‘иҫһиҒҢеҜ№дәҺиҮӘе·ұ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пјҢдё»иҰҒжҳҜеҜ№дёҚиө·дёӨдёӘдәә---жңұеҺҡжіҪе’ҢзҷҪзәӘе№ҙ(йҷ•иҘҝзңҒ委д№Ұи®°пјҢеӣ иғЎиҖҖйӮҰдёӢеҸ°иҖҢдёӢеҸ°)гҖӮеӣ дёәжңұеҺҡжіҪжҳҜеҸҜд»ҘеҪ“жҖ»д№Ұи®°зҡ„дёҖдёӘдәәгҖӮвҖқ
е…ӯеӣӣеҗҺжөҒдәЎжө·еӨ–зҡ„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е·ҘдҪңиҖ…гҖҒеӯҰдәәдҪ•йў‘пјҢжҠҠеҲӣеҠһеӨҡе№ҙзҡ„еӨҡз»ҙзҪ‘пјҢиҪ¬жүӢи®©з»ҷе•ҶдәәдәҺе“Ғжө·д№ӢеҗҺпјҢдё“еҝғеҠһе…¶жҳҺй•ңеҮәзүҲзӨҫгҖӮжңҖиҝ‘пјҢд»–иҝҳж”ҜжҢҒеҠһиө·дәҶдёҖд»ҪеҗҚдёәвҖңеӨ–еҸӮвҖқзҡ„жңҲеҲҠгҖӮиҝҷд»ҪжңҲеҲҠзҡ„еҸ‘еҲҠжңҹ(2010/1)дёҠпјҢе°ұжңүдёҖзҜҮжҠҘеҜјзҡ„йўҳзӣ®жҳҜпјҡеҺҹе®ҡжҺҘзҸӯдәәпјҢжңұеҺҡжіҪжүҚжҳҜиғЎиҖҖйӮҰдј дәәгҖӮ
жӣҫ經зҡ„йҰҷжёҜгҖҠдёғеҚҒе№ҙд»ЈгҖӢжқӮеҝ—зҡ„жқҺжҖЎе…Ҳз”ҹжңүеӣһжҶ¶и«ҮеҲ°жңұеҺҡжҫӨпјҢжқҺжҖЎиҜҙпјҡжңұеҺҡжіҪеңЁеҢ—дә¬еҢ»йҷўй©¬дёҠе°ұиҰҒеҠЁжүӢжңҜж—¶пјҢе—“еӯҗе“‘зқҖиҝҳиҰҒи·ҹе§ҡзӣ‘еӨҚиҜҙпјҡгҖҢдёӯеӣҪйҒ“и·ҜпјҢдёӯеӣҪжЁЎејҸдјҡдёҚдјҡеңЁ21дё–зәӘз»ҷдё–з•ҢеёҰжқҘзҒҫйҡҫпјҹдёӯеӣҪдјҡдёҚдјҡжҲҗдёә21дё–зәӘйӮӘжҒ¶еҠҝеҠӣпјҹ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жҲ‘и·ҹеҘҪеӨҡдәәи®ІдәҶпјҢдёҚд»ҘдёәжҳҜпјҢд№ҹдёҚж„ҝж„ҸзңӢжҲ‘жҸҗдҫӣзҡ„иҝҷдёӨжң¬д№ҰпјҢдҪ еҖ’еҗ¬дәҶжҲ‘иҜҙзҡ„иҜқпјҢзңӢдәҶиҝҷдёӨжң¬д№ҰпјҢиҰҒз»„з»ҮдәәеҘҪеҘҪз ”з©¶жү№еҲӨиҝҷдёӘпјҢеҗҰеҲҷдёӯеӣҪдјҡжҲҗдёә21дё–зәӘйӮӘжҒ¶еҠҝеҠӣгҖҚдёӯе…ұзҡ„дёӯеӣҪжЁЎејҸеҸ‘еұ•и·Ҝеҫ„еҚұе®іе…Ёдё–з•ҢгҖӮ
пјҲйӯҒзңҒеұұеҜЁВ·ж•ҙзҗҶеҢҜз·Ёпјү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