гҖҗ1966пҪһ2016ж–Үйқ©дә”еҚҒе№ҙдәҶгҖ‘пҪһ пјҲ2пјүи’ҷеҹҺиҖҒејөжңүиҜқиҜҙ
и’ҷеҹҺиҖҒејө-101698 03/15 47904.0/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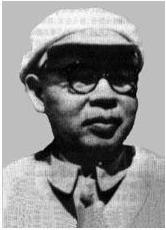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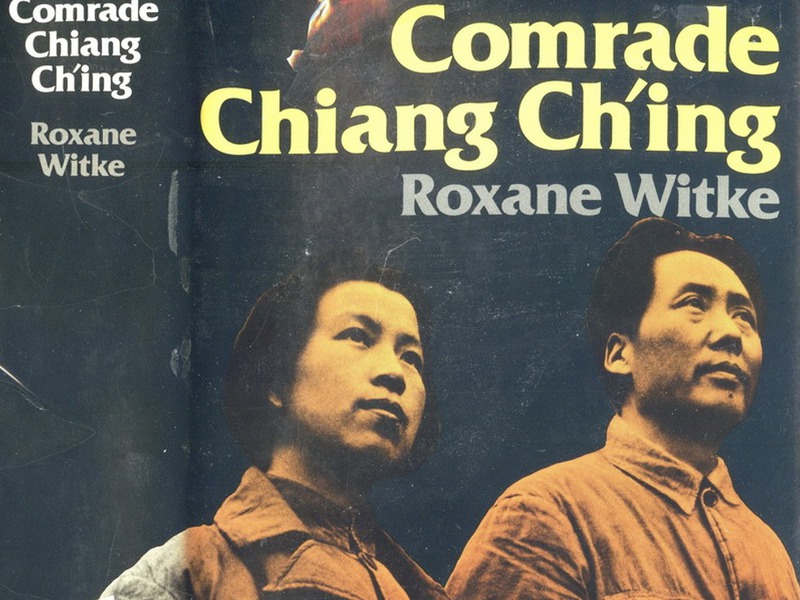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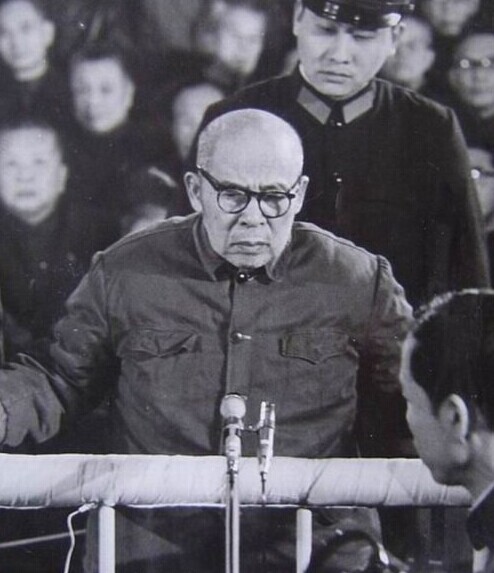

еҜ№дәҺеҺҶеҸІеҗ„з§Қз ”з©¶ж–Үз« пјҢеӣһеҝҶеҪ•..пјҢзӯүзӯүпјҢе°ҶиҝҮеҺ»зҡ„еҺҶеҸІи®°еҪ•пјҢе‘ҠзҹҘеҗҺдәәгҖӮдҪҶеҜ№ж–Үйқ©еҚҙдёҚиҝҷд№Ҳз®ҖеҚ•пјҢе®ғзҰ»жҲ‘们并дёҚйҒҘиҝңпјҢеҘҪеӨҡеҪ“дәӢдәәпјҢз»ҸеҺҶиҖ…пјҢеҸ—е®ідәәзӯүйғҪиҝҳеҒҘеңЁпјҢж–Үйқ©еҗҺйҒ—з—ҮеҜ№дёӯеӣҪзҡ„еҪұе“ҚдёҚз”ЁеӨҡиҜҙ..пјҢе®ғжңүеҸҜиғҪйҮҚжқҘ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ҙжҳҜеұҖйғЁзҡ„дёҖдәӣзҺ°иұЎйҮҚжј”..пјҢиҝҷдёҚжҳҜжӢ…еҝғзҘҳе‘ҪпјҢиҖҢжҳҜдёҚзҝ»еңҹпјҢдёҚйҷӨж №пјҢиҝҳдјҡй•ҝеҮәжҜ’иӢ—..пјҢиҝҷз»қдёҚжҳҜеҚұиЁҖиҖёеҗ¬вҖҰвҖҰгҖӮ д»ҠеӨ©пјҢејәеӣҪиҜёеӨҡйҖҖдј‘й«ҳе®ҳе®ҳеғҡиғҢжҷҜд№ӢдәәпјҢйҮҚиҝ”й«ҳж ЎпјҢзҺ©зҺ©ж–ҮеҢ–й«ҳйӣ…пјҢеңЁй«ҳж Ўи®ІеқӣдёҠйҮҚзҺ°еҪ“е№ҙеңЁдҪҚж—¶пјҢй«ҳи°Ҳйҳ”и®әзҡ„ж„ҹи§үпјҢи°Ҳж–ҮеҢ–гҖҒи°Ҳж•ҷиӮІпјҢи°ҲејәеӣҪжҠӨеҪҠд№Ӣзӯ–пјҢеҪ“然д№ҹиҰҒжқҘи°Ҳи®әеҸҚжҖқж–Үйқ©пјҢиҝҷеҪ“然жҳҜеҘҪдәӢпјҢжҳҜиҝӣжӯ©зҡ„иЎЁзҺ°..пјҢеҪ“然дҪ д№ҹдёҚиғҪиҰҒжұӮеӨӘеӨҡпјҢиҝҷдёӘеӨ§е®¶йғҪжҮӮзҡ„...гҖӮдҪҶжҲ‘е§Ӣз»Ҳи®ӨдёәпјҢиғҪеӨҹи°Ҳи®әжҜ”дёҚи°ҲеҘҪпјҢиғҪеӨҹеҸҚжҖқжҲ–иҖ…иҜҙеҸҚжҖқеҸӘеҲ°жҹҗдёҖдёӘзЁӢеәҰпјҢжҜ”дёҚеҸҚжҖқеҘҪ..пјҢиҝҷжҳҜжҲ‘дёӘдәәзҡ„дёҖиҙҜдё»еј гҖӮжҲ‘е»әи®®ејәеӣҪзҡ„зүӣдәәеӨ§и…•еңЁжңҖеҗҺдёҖи®ІйғҪеҠ дёҠдёҖиҠӮпјҢеҜ№иҮӘе·ұж–Үйқ©зҡ„еҸҚжҖқпјҢеҜ№иҮӘе·ұ家еәӯеңЁж–Үйқ©ж—¶зҡ„еҸҚжҖқпјҢеҜ№дҪ зҡ„зҲ¶жҜҚеңЁж–Үйқ©зҡ„еҸҚжҖқ...пјҢиҜҙдёҖиҜҙдҪ еңЁеӯҰж Ўжңүж— жү“иҝҮж Ўй•ҝпјҢеңЁйқ©е‘Ҫзҡ„жҝҖжғ…дёӢжңүж— иё©ж–ӯдҪ иҖҒйқ©е‘ҪзҲ¶жҜҚдәІзҡ„иӮӢйӘЁпјҢжңүж— еҗҗеҸЈж°ҙеңЁиҖҒеёҲи„ёдёҠ..пјҢжңүж— еҶҷиҝҮе‘ҠеҜҶдҝЎ..зӯүзӯүгҖӮиҜҙиҜҙеҳӣпјҢжҜҸдёҖдёӘдёӯеӣҪ家еәӯ..пјҢжҜҸдёӘдёӯеӣҪдәәйғҪиҜҙеҮә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дёҖе®ҡиҝӣжӯ©пјҒжҲ‘ж·ұдҝЎдёӘдәәзҡ„еҸҚжҖқеҸҚзңҒпјҢиҮӘжҲ‘еҗҜи’ҷпјҢжҲ‘ж·ұдҝЎдәәжҖ§зҡ„е–„иүҜпјҢжҲ‘ж·ұдҝЎдёҚ移дёӯеӣҪдјҡиҝӣжӯҘпјҢжҳҺеӨ©дјҡжӣҙеҘҪпјҒ еңЁжӯӨж‘ҳеҪ•йҷҲдјҜиҫҫзҲ¶еӯҗзҡ„иЁҖи®әпјҢйқһеёёеҖјеҫ—дёҖиҜ»пјҢиҝҷжҳҜдё»иҰҒж–Үйқ©е°Ҹз»„жҲҗе‘ҳеҸҠ家еәӯеҜ№ж–Үйқ©зҡ„еҸҚжҖқеҸҚзңҒпјҢж·ұеҲ»еҝҸжӮ”..пјҢд»ҘеҸҠжҒўеӨҚдәҶжӯЈеёёдәәжҖ§еҗҺпјҢеҜ№ж–Үйқ©зҡ„жҖқиҖғдёҺж·ұеҲ»жү№еҲӨ...гҖӮ з»ҸиҝҮж–Үйқ©зҡ„дәәйғҪзҹҘйҒ“йӮЈдёӘеҸЈйҹідёҚжё…зҡ„йҷҲдјҜиҫҫжӣҫжҳҜжқғеҠҝеҫҲеӨ§зҡ„第еӣӣеҸ·дәәзү©пјҢд»–дёҠйқўжҳҜжҜӣжіҪдёңгҖҒжһ—еҪӘгҖҒе‘ЁжҒ©жқҘгҖӮйҷҲжҳҜж”ҝжІ»еұҖ常委пјҢж–Үйқ©е°Ҹз»„з»„й•ҝпјҢжҳҜзӣҙжҺҘиҙҹиҙЈиҝҗеҠЁзҡ„йўҶеҜјдәәгҖӮж–Үйқ©д№Ӣе§ӢпјҢиҝ„д»Ҡиҝ‘еӣӣеҚҒе№ҙпјҢжңүе…іжҜӣжіҪдёңжһ—е‘Ёзҡ„дј и®°гҖҒж–ҮиүәдҪңе“ҒдёҚеҸҜиғңж•°пјҢжңүе…іжұҹйқ’еӣӣдәәеё®е’Ңиў«жү“еҖ’зҡ„еҲҳгҖҒйӮ“гҖҒйҷ¶зҡ„дҪңе“Ғд№ҹдёҚе°‘пјҢе”ҜзӢ¬еҜ№иҝҷдҪҚеӣӣеҸ·дәәзү©зҡ„дҪңе“Ғз”ҡдёәзҪ•и§ҒпјҢд»Ҙдё“и‘—иҖҢи®әпјҢд»…дёҖжң¬еҸ¶ж°ёзғҲз»ҸиҝҮе®ҳж–№е®Ўйҳ…зҡ„гҖҠйҷҲдјҜиҫҫдј гҖӢпјҢжңүе…ійҷҲзҡ„и®°иҪҪеҲҶж•ЈеңЁжңүе…іж–Үйқ©зҡ„еҗ„з§Қж–Үеӯ—дёӯгҖӮйҷҲдјҜиҫҫд№ӢеӯҗйҷҲжҷ“еҶңзј–ж’°зҡ„гҖҠйҷҲдјҜиҫҫжңҖеҗҺеҸЈиҝ°еӣһеҝҶгҖӢпјҢжҳҜејҘиЎҘеҜ№йҷҲдјҜиҫҫз ”з©¶д№ӢдёҚи¶ізҡ„дёҖжң¬йҮҚиҰҒи‘—дҪңгҖӮ
йҷҲдјҜиҫҫд№Ӣе„ҝйҷҲжҷ“еҶңиҜҙдәҶдёҖж®өеҫҲж·ұеҲ»гҖҒеҫҲеҲ°дҪҚзҡ„иҜқпјҢеҰӮдёӢпјҡ вҖңеҫҲе°‘жңүдәәи°Ҳ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еүҚ30е№ҙзҡ„жҲҗе°ұе’ҢеҗҺ30е№ҙзҡ„жҲҗе°ұжҳҜд»Җд№Ҳе…ізі»гҖӮиҰҒзЁҚеҫ®жғідёҖжғіе°ұдјҡеҸ‘зҺ°пјҢиҝҷйҮҢйқўеӯҳеңЁдёҖдёӘеҫҲеӨ§зҡ„жӮ–и®әгҖӮж”№йқ©зҡ„еҜ№иұЎжҳҜд»Җд№Ҳе‘ўпјҹж”№йқ©ж”№зҡ„дёҚжҳҜ60е№ҙеүҚеӣҪж°‘е…ҡж—¶д»Јзҡ„дҪ“еҲ¶пјҢж”№йқ©ж”№зҡ„жӯЈеҘҪжҳҜйқ©е‘Ҫзҡ„жҲҗжһңпјҢж”№зҡ„е°ұжҳҜ30е№ҙйқ©е‘Ҫзҡ„и®ЎеҲ’з»ҸжөҺгҖҒдәәж°‘е…¬зӨҫгҖҒе…¬жңүеҲ¶гҖӮжҚўеҸҘиҜқи®ІпјҢж”№йқ©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еҜ№йқ©е‘Ҫе’Ң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е»әи®ҫзҡ„е…ЁзӣҳеҗҰе®ҡгҖӮеҶҚиҝӣдёҖжӯҘзңӢпјҢ60е№ҙиө°дёӢжқҘзҡ„з»“жһңжҳҜдёӯеӣҪеңЁз»ҸжөҺдҪ“еҲ¶йҮҚж–°еӣһеҲ°дәҶеҺҹзӮ№пјҢеӣһеҲ°дәҶ1949е№ҙд»ҘеүҚгҖӮд»ҠеӨ©дёӯеӣҪи®І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еҸ–еҫ—е·ЁеӨ§зҡ„жҲҗе°ұпјҢдёӯеӣҪеҲқжӯҘе»әз«ӢдәҶ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дҪ“еҲ¶гҖӮеҸҜжҳҜпјҢжҲ‘们еҸҜд»Ҙй—®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пјҢ1949е№ҙд»ҘеүҚдёӯеӣҪд»Җд№ҲдҪ“еҲ¶пјҹйӮЈж—¶еҖҷдёӯеӣҪе°ұжҳҜ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дҪ“еҲ¶гҖӮйӮЈж—¶еҖҷд№ҹеҜ№еӨ–ејҖж”ҫпјҢжүҖжңүзҡ„дәәжғіеҮәеӣҪе°ұеҮәеӣҪпјҢжІЎжңүжҺ§еҲ¶зҡ„пјҢеҫҲиҮӘз”ұгҖӮйӮЈд№Ҳ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дёӯеӣҪиҰҒз”Ёйқ©е‘ҪеҺ»жҠҠеёӮеңәз»ҸжөҺдҪ“еҲ¶ж¶ҲзҒӯдәҶпјҢиҠұдәҶ30е№ҙж—¶й—ҙпјҢ然еҗҺеҶҚиҠұ30е№ҙеҶҚжҠҠе®ғйҮҚж–°е»әз«Ӣиө·жқҘпјҹвҖқ вҖңдёӯеӣҪ1949еҗҺиҝҷеңәзҝ»еӨ©иҰҶең°зҡ„йқ©е‘ҪеҲ°еә•еёҰжқҘдәҶд»Җд№Ҳпјҹз»“и®әе…¶е®һеҫҲз®ҖеҚ•пјҢд»–еҸӘжҳҜжҠҠеҺҹжқҘзҡ„з»ҹжІ»йҳ¶зә§жҺЁзҝ»дәҶпјҢжҠҠеҺҹжқҘжёёзҰ»еңЁзӨҫдјҡеә•еұӮжғійҖ еҸҚзҡ„дёҖдәӣең°з—һгҖҒжөҒж°“пјҢиҜҙеҘҪеҗ¬зӮ№жҳҜйҖ еҸҚиҖ…гҖҒйқ©е‘ҪиҖ…пјҢиҜҙйҡҫеҗ¬зӮ№е°ұжҳҜдёҖзҫӨеңҹеҢӘгҖҒең°з—һе’ҢдёҖдәӣеҸЈеҸЈеЈ°еЈ°жҗһйқ©е‘Ҫзҡ„е°Ҹж–ҮдәәпјҢеҗёж”¶еҲ°жүҖи°“зҡ„йқ©е‘ҪйҳҹдјҚдёӯжқҘжҲҗдёәйӘЁе№ІеҲҶеӯҗпјҢжңҖеҗҺиҝҷдәӣдәәжҺҢжҸЎдәҶж”ҝжқғпјҢжҲҗдёәж–°зҡ„з»ҹжІ»йҳ¶зә§гҖӮзҺ°еңЁд»–们зҡ„еӯҗеӯҷз»ҹжІ»зқҖдёӯеӣҪ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жҲҗдёәдәҝдёҮеҜҢзҝҒ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йқ©е‘ҪдёҚиҝҮе°ұжҳҜжҚўдёҖжү№дәәеҸ‘иҙўиҖҢе·ІвҖ”вҖ”иҝҷжү№ж–°еҸ‘иҙўзҡ„дәәжӣҙзіҹзі•пјҒиҝҮеҺ»зҡ„з»…еЈ«йҳ¶зә§иҝҳжңүзӮ№зҹҘд№ҰиҫҫзӨјпјҢиҝҳжңүдёҖзӮ№дјҰзҗҶеёёиҜҶпјҢиҖҢд»ҠеӨ©дёӯеӣҪзҡ„з»ҹжІ»йҳ¶зә§-вҖ”вҖ”дёӯеӣҪзҡ„зІҫиӢұйҮҢйқўжҲ‘们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пјҢ他们зҡ„ж–ҮеҢ–еұӮж¬ЎжҜ”еҺҶеҸІдёҠеҺҶд»Је®ҳеғҡиҝҳиҰҒе·®гҖӮеӣ дёәдёӯеӣҪд»ҺжқҘжІЎжңүиҝҮе®ҳеғҡеҗғе–қе«–иөҢеҲ°зҺ°еңЁиҝҷдёӘзЁӢеәҰгҖӮеҰӮжһңз”ЁвҖңи…җеҢ–вҖқжқҘеҪўе®№пјҢд»ҠеӨ©зҡ„дёӯеӣҪе®ҳеғҡи…җеҢ–зЁӢеәҰпјҢеңЁеҺҶеҸІдёҠд№ҹжҳҜ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пјҢиҫҫеҲ°зҷ»еі°йҖ жһҒзҡ„вҖң!
йҷҲдјҜиҫҫпјҲ1904в”Җ1989пјүпјҢзҰҸе»әжіүе·һдәәпјҢеңЁдёӯе…ұй«ҳеұӮд№ жғҜз§°д»–гҖҢиҖҒеӨ«еӯҗгҖҚгҖӮд»–еңЁеӣҪе…ұеҲҶиЈӮзҡ„дёҖд№қдәҢдёғе№ҙеҠ е…Ҙдёӯе…ұпјҢеҗҢе№ҙиөҙиҺ«ж–Ҝ科дёӯеұұеӨ§еӯҰе°ұиҜ»пјҢдёүе№ҙеҗҺеӣһеӣҪпјҢеҒҡе…ҡзҡ„е®Јдј е·ҘдҪңпјҢзј–жқӮиӘҢпјҢеҶҷж–Үз« пјҢеҗҢж—¶з ”з©¶ж–ҮеҸІй—®йўҳпјҢеңЁеҢ—дә¬дёӯеӣҪеӨ§еӯҰд»»ж•ҷпјҢ并еҸ‘еҠЁдёҖеңәжңүе…ЁеӣҪеҪұе“Қзҡ„гҖҢж–°еҗҜи’ҷиҝҗеҠЁгҖҚгҖӮдёҖд№қдёүдёғе№ҙиҝӣе…Ҙ延е®үпјҢдёҖе№ҙеҗҺе’ҢжҜӣжіҪдёңдәӨжөҒеҸӨд»Је“ІеӯҰз ”з©¶иҖҢжҲҗдёә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ж”ҝжІ»з§ҳд№ҰгҖӮд»ҺжӯӨпјҢеңЁй•ҝиҫҫдёүеҚҒе№ҙжңҹй—ҙпјҢд»–дҪңдёә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дёҖжһқ笔пјҢеҸӮдёҺиө·иҚүи®ёеӨҡе…ҡзҡ„йҮҚиҰҒж–Ү件гҖҒеҶіи®®гҖҒи‘—дҪң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ж–Үз« гҖҒи®ІиҜқпјҢд№ҹеҸӮдёҺжҹҗдәӣеҶізӯ–пјҢзӣҙиҮідёҖд№қдёғв—Ӣе№ҙеәҗеұұдјҡи®®иў«жҜӣжіҪдёңзӮ№еҗҚжү“еҖ’гҖӮ
йҷҲдјҜиҫҫдҝқеӨ–жңҹй—ҙд»ҚдёҚж–ӯеҶҷдҪңпјҢеҢ…жӢ¬е“ІеӯҰгҖҒж–ҮеҸІиҜ„и®әпјҢз”ҡиҮіжңүз»ҸжөҺи®әж–ҮгҖӮеҸ¶ж°ёзғҲжӣҫеӨҡж¬Ўи®ҝй—®иҝҮйҷҲдјҜиҫҫпјҢд№қе…«е№ҙзҡ„дҝ®и®ўж–°зүҲйҷҲдј иҝҳеҫ—еҲ°йҷҲжҷ“еҶңи®ёеӨҡеё®еҠ©гҖӮйӮЈд№ҲпјҢд»ҠеӨ©йҷҲжҷ“еҶңеҶҚеҮәиҝҷжң¬еҸЈиҝ°еӣһеҝҶеҪ•пјҢеҝ…然жңүеҸ¶дј зҡ„и®ёеӨҡжңӘе°ҪжҲ–жӯ§ејӮд№ӢеӨ„гҖӮжҲ‘зңӢе·®еҲ«еңЁдәҺпјҢжҷ“еҶңж–°и‘—жӣҙзқҖйҮҚеңЁжҫ„жё…иҫ©жӯЈдәӢе®һж–№йқўпјҢеӣ дёәйҷҲдјҜиҫҫжңҖеҗҺе…«е№ҙпјҢд»ҚеӨ„дәҺдёҺеӨ–з•Ңйҡ”зҰ»зҠ¶жҖҒпјҢе…¶еӯҗжҷ“еҶңжҳҜжңқеӨ•йҷӘдјҙз…§ж–ҷд»–з”ҹжҙ»зҡ„е”ҜдёҖзҡ„еӯҗеҘіпјҲйҷҲд№Ӣй•ҝеӯҗдёҖд№қе…ӯв—Ӣе№ҙеӣ дёҺжҜӣжіҪдёңеҘіжқҺж•ҸзӣёзҲұеӨұжҒӢиҖҢиҮӘжқҖжӯ»пјүпјҢжҷ“еҶңи®°еҪ•дәҶи®ёеӨҡдёҺзҲ¶дәІзҡ„и°ҲиҜқпјҢжҲҗдёәжң¬д№Ұзҡ„иө„ж–ҷжқҘжәҗгҖӮ
жҷ“еҶңд»Ҙе…¶зҲ¶дёҖд№қдәҢдә”е№ҙдёҖзҜҮе°ҸиҜҙзҡ„дёҖж®өиҜқдҪңдёәйҷҲдјҜиҫҫдёҖз”ҹеқҺеқ·зҡ„еҶҷз…§пјҡгҖҢжҲ‘зҺ°еңЁжӯЈеҰӮйӮЈжҜҸж¬ЎйғҪжү“иҙҘдәҶд»—зҡ„д№…з»ҸжҲҳйҳөзҡ„е…өеЈ«пјҢйҒҚиә«иҙҹзқҖдјӨз—•пјҢеҖ’еҚ§еңЁжҡ®иүІиӢҚеҮүзҡ„иҚүйҮҺйҮҢпјҢжңӣзқҖиҘҝеұұзҡ„ж®ӢйҳіеңЁиӢҹ延ж®Ӣе–ҳгҖӮгҖҚжӮІжҖңд№Ӣжғ…пјҢжәўдәҺиЁҖиЎЁгҖӮ
жҜӣжіҪдёңеҜ№йҷҲзҡ„дҝЎд»»пјҢеңЁдёӯе…ұйҳөиҗҘзҡ„зҹҘиҜҶд»ҪеӯҗдёӯпјҢж— еҮәе…¶еҸігҖӮ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дёғеӨ§жҠҘе‘ҠпјҢдёӨж¬ЎиөҙиӢҸйЎҫй—®гҖҒе…ұеҗҢзәІйўҶе®Әжі•иҚүжЎҲгҖҒе…«еӨ§жҠҘе‘ҠгҖҒжү№иӢҸе…ұдәҢеҚҒеӨ§ж–Үз« гҖҒжҜӣжіҪдёңи®әеҚҒеӨ§е…ізі»гҖҒеӣҪйҷ…е…ұиҝҗдәҢеҚҒдә”жқЎгҖҒдёғеҚғдәәеӨ§дјҡеҲҳе°‘еҘҮжҠҘе‘ҠгҖҒж–Үйқ©еҚҒе…ӯжқЎ ...... еӨ§еӨҡеҮәиҮӘйҷҲзҡ„иҚүзЁҝгҖӮ
д№ҰдёӯжҸҸиҝ°йҷҲдјҜиҫҫеҜ№жҜӣеҲҳзҹӣзӣҫзҡ„зңӢжі•дёҺд»Ӣе…ҘпјҢжңүзӢ¬еҲ°д№ӢеӨ„гҖӮд»–иҜҙпјҢжҜӣеҲҳеҲҶжӯ§еңЁеӣӣжё…й—®йўҳдёҠжҒ¶еҢ–пјҢдёҚжҳҜеҲҳеҗҰи®Ө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пјҢиҖҢжҳҜеҲҳи®Өдёәй—®йўҳеңЁеҹәеұӮпјҢеңЁдёӢйқў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еҲҷи®ӨдёәеңЁе…ҡеҶ…пјҢеңЁеҪ“жқғжҙҫгҖӮеңЁжҜӣеҲҳд№ӢдәүдёӯпјҢйҷҲз«ҹеҸҜд»Ҙж–ҪеҠ еҪұе“ҚпјҢзј“е’ҢеҸҢж–№е…ізі»гҖӮд»–дё»еҠЁеҗ‘жҜӣжіҪдёңе»әи®®з”ұеҲҳжҖ»з®Ўеӣӣжё…пјҢдёәжҜӣжіҪдёңйҮҮзәіпјҢеҚіжүҫеҲҳи°ҲиҜқгҖӮйҷҲиҜҙпјҢеҲҳеңЁеӨ–йқўеҪўиұЎжё©е’ҢпјҢе®һеҲҷеҒҡдәӢжӯҰж–ӯпјҢдёҚеҘҪе•ҶйҮҸпјҢи„ҫж°”е’ҢжҜӣжіҪдёңе·®дёҚеӨҡгҖӮе…ӯдә”е№ҙдёҖжңҲеҸ‘з”ҹиҝҮдёҖ件еҲҳеҫ—зҪӘ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дәӢгҖӮеңЁдёӯеӨ®дјҡи®®дёҠ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еҲҡеҸ‘иЁҖдёҚд№…пјҢе°ұиў«еҲҳжү“ж–ӯжҸ’иҜқпјҢиҖҢдё”пјҢдёҖи·ҜиҜҙдёӢеҺ»пјҢи§ҶжҜӣжіҪдёңдёәж— зү©гҖӮжҜӣжіҪдёң第дәҢеӨ©ејҖдјҡпјҢе°ұдёҫзқҖе…ҡз« иҜҙе…ҡе‘ҳжңүеҸ‘иЁҖжқғпјҢжҡ—жҢҮеҲҳдёҚи®ёд»–еҸ‘иЁҖ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еҜ№ж–ҜиҜәиҜҙпјҢйӮЈж¬Ўдјҡи®®еҗҺпјҢд»–еҶіе®ҡеҲҳиҰҒдёӢеҸ°гҖӮ
йҷҲдјҜиҫҫиҜҙпјҢйӮЈж¬ЎдјҡеҗҺ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иҰҒд»–иө·иҚүдәҢеҚҒдёүжқЎпјҢд»–ж„ҹеҲ°жҜӣжіҪдёңеҜ№еҲҳжңүгҖҢеҫҲеӨ§ж„Ҹи§ҒгҖҚпјҢеҝғйҮҢдёҚе®үпјҢдҫҝжүҫдәҶзҺӢеҠӣгҖҒеҪӯзңҹгҖҒйҷ¶й“ёеҺ»е’ҢеҲҳи°ҲпјҢзӣјеҲҳеҒҡжЈҖи®ЁгҖӮдёәи°ғе’ҢжҜӣжіҪдёңеҲҳе…ізі»пјҢд»–гҖҢеҒҡиҝҮеҮ ж¬ЎеҠӘеҠӣгҖҚ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е‘ЁйғҪеҫҲжё…жҘҡгҖӮжҜӣжіҪдёңеҗҺжқҘжү№иҜ„д»–еңЁжҜӣжіҪдёңеҲҳд№Ӣй—ҙгҖҢжҗһжҠ•жңәгҖҚеҚіжҢҮжӯӨгҖӮйҷҲеӣһзӯ”жҷ“еҶңй—®иҜҙпјҡеҲҳдёҠеҸ°жҳҜдёҚжҳҜиө°иө„жң¬дё»д№үйҒ“и·Ҝпјҹд»–дёҚиӮҜе®ҡпјҢдҪҶиӮҜе®ҡдјҡе®һзҺ°дёӯиӢҸе’ҢеҘҪгҖӮеҚіеҲҳдёҚдјҡеҸҚдҝ®пјҢиҝҷжҳҫ然жҳҜжҜӣжіҪдёңеҲҳзҡ„йҮҚеӨ§еҲҶжӯ§гҖӮйҷҲиҜҙпјҢеҲҳеҜ№еӨ§и·ғиҝӣд№ҹдёӢиҝҮдёҚе°‘й”ҷиҜҜжҢҮзӨәгҖӮе…ӯдәҢе№ҙиҮіе…ӯдә”е№ҙд»Ҙ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дёәзәІзҡ„и·ҜзәҝеҪўжҲҗ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жңүдё»иҰҒиҙЈд»»пјҢе…¶д»–дәәд№ҹжңүиҙЈд»»пјҢд»–жң¬дәәд№ҹжҺҘеҸ—иҝҷжқЎи·ҜзәҝпјҢеё®жҜӣжіҪдёңеҲҳи®°еҪ•дёҖдәӣжҢҮзӨәпјҢдҪҶиҝҷжқЎиҙҜз©ҝд№қеӨ§гҖҒиҮіеҚҒдёҖеӨ§зҡ„и·Ҝзәҝзҡ„гҖҢ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–Үеӯ—иЎЁиҫҫв”Ӯв”ӮжҜӣжіҪдёңеңЁе…«еұҠеҚҒдёӯе…ЁдјҡдёҠе…ідәҺгҖҢ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иҰҒе№ҙе№ҙи®ІгҖҒжңҲжңҲи®ІгҖҒеӨ©еӨ©и®ІгҖҚзҡ„дёҖж®өиҜқпјҢеҚҙжҳҜзҺӢеҠӣиҖҢдёҚжҳҜйҷҲдјҜиҫҫж•ҙзҗҶзҡ„гҖӮеҚҒеӨ§жӣҙжү№йҷҲеҸҚеҜ№гҖҢж— дә§йҳ¶зә§дё“ж”ҝдёӢ继з»ӯйқ©е‘ҪгҖҚгҖӮ
гҖҖ иө·иҚүдёҖд№қдә”е…ӯе№ҙдёӯе…ұе…«еӨ§ж”ҝжІ»жҠҘе‘ҠеҶіи®®дёӯпјҢжҸҗеҮәеҜ№еӣҪеҶ…дё»иҰҒзҹӣзӣҫзҡ„иЎЁиҝ°пјҡгҖҢжҳҜе…Ҳиҝӣзҡ„зӨҫдјҡдё»д№үеҲ¶еәҰеҗҢиҗҪеҗҺзҡ„зӨҫдјҡз”ҹдә§еҠӣд№Ӣй—ҙзҡ„зҹӣзӣҫгҖӮгҖҚдҪҶдјҡеҗҺжҜӣжіҪдёңиЎЁзӨәејӮи®®пјҢи®ӨдёәеӣҪеҶ…зҹӣзӣҫе®һиҙЁжҳҜгҖҢж— дә§йҳ¶зә§дёҺиө„дә§йҳ¶зә§зҡ„зҹӣзӣҫгҖӮгҖҚ дёҖд№қе…ӯдә”е№ҙиө·иҚүгҖҠе·Ҙдёҡй—®йўҳгҖӢж–Ү件пјҢдё»еј гҖҢз”өеӯҗдёәдёӯеҝғгҖҚеҸ‘еұ•е·Ҙдёҡ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еҪ“ж—¶иҝҳзӣёеҪ“иөһи®ёгҖҒй«ҳе…ҙпјҢз ҙдҫӢең°еҚ•зӢ¬иҜ·йҷҲеҗғйҘӯгҖӮдҪҶйҒӯеҲ°йӮ“е°Ҹе№іеҸҚеҜ№пјҢиҜҙжҗһеӨӘеӨҡж–°жҠҖжңҜпјҢдёҚеҗҲйҖӮпјҢиҰҒд»Ҙй’ўдёәзәІпјҢеӨ§е®¶ж— иЁҖпјҢж–Ү件被еҗҰе®ҡгҖӮ
гҖҖ иө·иҚүдёҖд№қе…ӯд№қе№ҙд№қеӨ§жҠҘе‘Ҡж—¶пјҢйҷҲжҸҗеҮәд»ҘеҗҺиҰҒд»ҘжҗһеҘҪз”ҹдә§жҸҗй«ҳз”ҹдә§зҺҮдёәдё»иҰҒд»»еҠЎпјҢеҸҲжү№иҜ„иҝҮеј жҳҘжЎҘгҖҒе§ҡж–Үе…ғиө·иҚүзҡ„жҠҘе‘ҠжҳҜдјҜжҒ©ж–ҜеқҰи§ӮзӮ№гҖҢиҝҗеҠЁе°ұжҳҜдёҖеҲҮпјҢзӣ®зҡ„жҳҜжІЎжңүзҡ„гҖҚгҖӮиў«жҜӣжіҪдёңжҙҫжүҖжӢ’з»қпјҢж–ҘдёәгҖҢе”Ҝз”ҹдә§еҠӣи®әгҖҚгҖҒгҖҢдҝ®жӯЈдё»д№үгҖҚгҖӮжҜӣжіҪдёңеҜ№йҷҲзҡ„иҚүзЁҝпјҢеҺҹе°ҒдёҚеҠЁйҖҖеӣһпјҢиҝҳиҜҙйҷҲжҳҜгҖҢиҲ№иҰҒжІүдәҶпјҢиҖҒйј жҗ¬е®¶гҖҚпјҢжҢҮйҷҲиҰҒиғҢеҸӣд»–пјҢдёҚжҗһиҝҗеҠЁпјҢиҰҒжҗһз”ҹдә§дәҶгҖӮиҜҙйҷҲжң¬жҖ§йҡҫж”№пјҢжҖ»жҳҜзңӢйҮҚз»ҸжөҺпјҢгҖҢеёқеӣҪдё»д№үжң¬жҖ§дёҚж”№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жң¬жҖ§д№ҹдёҚж”№гҖӮгҖҚ
йҷҲжҷ“еҶңиҝҷжң¬д№ҰеҢ…еҗ«дёҖдәӣйҷҲдјҜиҫҫйҖҸйңІзҡ„е°‘и§Ғзҡ„й«ҳеұӮеҶ…幕гҖӮдҫӢеҰӮпјҡдёәе‘ЁжҒ©жқҘиҜҙжғ…гҖӮеҰӮеүҚиҝ°йҷҲдјҜиҫҫи°ғе’ҢиҝҮжҜӣжіҪдёңеҲҳе…ізі»пјҢд№ҹдёәжҜӣжіҪдёңе‘Ёе…ізі»и§ЈиҝҮеҘ—гҖӮж–Үйқ©еҲқжңҹпјҢдёҖеӨ©пјҢйӮ“йўҚи¶…зӘҒжқҘжӢңи®ҝйҷҲдјҜиҫҫеӨ«дәәеҲҳеҸ”е®ҙпјҢеҺҹжқҘе‘ЁжҒ©жқҘеҸ—дәҶ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йҮҚиҜқжү№иҜ„пјҢеҝғжғ…дҪҺиҗҪе·ІеҪұе“Қж—Ҙеёёе·ҘдҪңпјҢйӮ“зӣјйҷҲеҸҜд»Ҙеұ…дёӯи°ғе’ҢпјҢйҷҲеҲҷеӨҡж¬ЎеңЁжҜӣжіҪдёңйқўеүҚдёәе‘Ёзј“йўҠпјҢдҪҝе‘Ёж‘Ҷи„ұеӣ°еўғгҖӮж–Үйқ©еҗҺйӮ“йўҚи¶…дәҰжҠ•жЎғжҠҘжқҺпјҢеә”йҷҲиҰҒжұӮдёәйҷҲеҰ»е№іеҸҚпјҢи°ғдёӯеҠһзҰ»дј‘гҖӮиҷҪ然еҘ№е·ІдёҺйҷҲзҰ»е©ҡпјҢеҸҢж–№з»ҲжңӘз ҙй•ңйҮҚеңҶгҖӮ
гҖҖ дёҺжұҹйқ’е…ізі»гҖӮйҷҲеңЁеәҗеұұдјҡи®®еүҚжӣҫдёҺе‘ЁжҒ©жқҘи°ҲеҲ°жұҹйқ’еҜ№жҜӣжіҪдёңдёҚеҝ е®һпјҢеҘ№дёүж¬ЎеҜ№йҷҲиҜҙиҰҒзҰ»ејҖжҜӣжіҪдёңпјҢ第дёҖж¬ЎеңЁе»¶е®үжһЈеӣӯпјӣ第дәҢж¬ЎеңЁиҘҝжҹҸеқЎпјҢжұҹиҜҙиҰҒзҰ»ејҖжҜӣжіҪдёңеҺ»еҲ«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ӣ第дёүж¬ЎеңЁеҢ—дә¬иҘҝеұұпјҢи§Јж”ҫеҗҺгҖӮе‘ЁиҜҙ第дёүж¬ЎпјҢд»–зҹҘйҒ“пјҢжҳҜжҜӣжіҪдёңиҰҒе‘ЁжҠҠеҘ№йҖҒеҲ°иҺ«ж–Ҝ科еҺ»зҡ„гҖӮжңүдёҖж¬ЎжұҹжқҘеҲ°йҷҲеҠһе…¬е®ӨпјҢзңӢеҲ°д№Ұжһ¶дёҠжңүе®ӢеәҶйҫ„ж–ҮйӣҶпјҢжҠҪеҮәжқҘе°ұеҫҖең°жқҝдёҠж‘”гҖӮеҸҲдёҖж¬ЎејҖдјҡпјҢжұҹиҫұйӘӮйҷҲж”»еҮ»жқҺеёҢеҮЎпјҢйҡҸеҚіеҸ«жқҺеҮәжқҘпјҢдәҢдәәжҠұеӨҙеӨ§е“ӯпјҢжҠҠзҺ»з’ғжқҜж‘”зўҺеңЁйҷҲи„ҡдёӢпјҢйҷҲеҸӘеҫ—еҺ»жӢҫиө·дёҖең°зҡ„зўҺзүҮгҖӮ
гҖҖ йҷҶе®ҡдёҖж–Үйқ©еүҚеҫҲе·ҰгҖӮдёҖд№қе…ӯдәҢе№ҙе№ҝе·һдјҡи®®дёҠе‘ЁжҒ©жқҘйҷҲжҜ…з»ҷзҹҘиҜҶд»Ҫеӯҗж‘ҳиө„дә§йҳ¶зә§еёҪеӯҗ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ж— ејӮи®®пјҢдҪҶеҗҺж— дёӢж–ҮпјҢеҺҹжқҘе…ҡеҶ…жңүдәәеҸҚеҜ№гҖӮдёӯе®ЈйғЁй•ҝйҷҶе®ҡдёҖиҜҙзҹҘиҜҶд»ҪеӯҗжІЎз”ҡд№ҲеҸҳеҢ–пјҢдёҚиғҪж‘ҳеёҪпјҢе’Ңе‘ЁжҒ©жқҘжҝҖзғҲдәүжү§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жҺҘеҸ—йҷҶ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е…ӯеӣӣе№ҙ并з”ұйҷҶеҮәд»»ж–ҮеҢ–йғЁй•ҝд»ЈжӣҝиҢ…зӣҫгҖӮдёҚиҝҮеҘҪжҷҜдёҚй•ҝпјҢе…ӯдә”е№ҙйҷҶеӣ еӨ«дәәдёҘж…°еҶ°еҢҝеҗҚдҝЎеҸҚжһ—еҪӘдәӢ件иҖҢж Әиҝһж’ӨиҒҢпјҢе…ӯе…ӯе№ҙж–Үйқ©еүҚжӣҙиў«жү“жҲҗеҸҚе…ҡйӣҶеӣўгҖӮжҚ®иҜҙж–Үйқ©еҗҺпјҢйҷҶжҳҜеқҡеҶідё»еј жү№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пјҢд»–ж–Үйқ©еүҚзҡ„е·ҰеҸІпјҢдҫҝдёәе°ҠиҖ…и®ідәҶгҖӮжҷ“еҶңжҢҮеҮәпјҢйҷҶеңЁе…ӯеӣӣе№ҙеә•дёӯеӨ®дјҡи®®дёҠи®Іж–ҮеҢ–йқ©е‘ҪпјҢгҖҢиҜҙж–ҮеҢ–йғЁе…ЁзғӮжҺүдәҶпјҢжҳҜиө„дә§йҳ¶зә§е°Ғе»әйҳ¶зә§иҒ”еҗҲдё“ж”ҝгҖҚпјҢеҜ№жҜӣжіҪдёңеҸ‘еҠЁж–ҮеҢ–еӨ§йқ©е‘ҪжңүйҮҚиҰҒеҪұе“ҚгҖӮ
еҸҚеҸіиҝҗеҠЁдёҺеәҗеұұдјҡи®®и§’иүІ
йҷҲдјҜиҫҫеҸҚеҸіиҝҗеҠЁиЎЁзҺ°еҰӮдҪ•пјҹжҷ“еҶңд№Ұеј•иҜҒзҲ¶дәІи°ҲиҜқдёҺиө„ж–ҷпјҢйҰ–е…ҲпјҢдә”дёғе№ҙдәҢжңҲ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дҪңжӯЈзЎ®еӨ„зҗҶдәәж°‘еҶ…йғЁзҹӣзӣҫзҡ„и®ІиҜқпјҢдёҺйҷҲиҮҙжҜӣжіҪдёңдёҖдҝЎжңүе…іпјҢиҖҢеҸ‘иЎЁзҡ„и®ІиҜқд№ҹжҳҜйҷҲж•ҙеҹӢжҲҗж–Үзҡ„.ж–ҮдёӯйҷҲдјҜиҫҫеҺҹеҠ жңүгҖҢеӨ§и§„жЁЎзҫӨдј—жҖ§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е·Із»Ҹз»“жқҹгҖҚд№ӢеҸҘпјҢеҗҺж”№дёәеҒҸе·Ұзҡ„жҸҗжі•пјҢжҳҜжҜӣжіҪдёңжҺҘеҸ—йҷҲжӯЈдәәзҡ„ж„Ҹи§ҒиҖҢе®ҡзҡ„гҖӮеҸҚеҸіжңҹй—ҙ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жІЎжңүеҶҷдёҖзҜҮж–Үз« пјҢиҖҢиғЎд№”жңЁдёәдәәж°‘ж—ҘжҠҘеҶҷ
дәҶеӨҡзҜҮеҸҚеҸізӨҫи®әгҖӮжҜӣжіҪдёңжӣҫжҙҫйҷҲеҺ»еҢ—еӨ§зңӢеӨ§еӯ—жҠҘпјҢйҷҲзңӢеҗҺжҠҘе‘ҠиҜҙгҖҢдёҚеҖјеҫ—еӨ§жғҠе°ҸжҖӘпјҢжІЎз”ҡд№ҲдёҚеҫ—дәҶгҖӮгҖҚеҪ“ж—¶пјҢйӮ“е°Ҹе№ідё»жҢҒдёҖж¬ЎзңҒеёӮ委д№Ұи®°дјҡи®®гҖҢиҜҙзҺ°еңЁж—¶й—ҙжҜ”йҮ‘еӯҗиҝҳе®қиҙөпјҢиҰҒд№Ұ记们иө¶еҝ«еӣһеҺ»ж”¶йӣҶеҸіжҙҫиЁҖи®әпјҢеҗҰеҲҷжҷҡдәҶпјҢ收йӣҶдёҚеҲ°дәҶгҖӮгҖҚйҷҲеҗ¬еҲ°гҖҢеҫҲжғҠ讶гҖҚ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пјҢдәәжҖ»дјҡиҜҙй”ҷиҜқзҡ„пјҢиҝҷж ·ж”¶йӣҶпјҢзүөж¶үеӨӘеӨҡпјҢгҖҢеҸҚеҸіжҗһеҫ—йӮЈж ·жү©еӨ§еҢ–пјҢйӮ“е°Ҹе№іеҗҢеҝ—жңүеҫҲеӨ§иҙЈ
д»»гҖӮгҖҚ
еҪ“е№ҙд№қжңҲпјҢйӮ“еңЁдёүдёӯе…ЁдјҡдҪңж•ҙйЈҺеҸҚеҸіжҠҘе‘ҠпјҢжҠҠзҹҘиҜҶд»Ҫеӯҗе’Ңиө„дә§йҳ¶зә§ж”ҫеңЁдёҖиө·жү“еҮ»пјҢиҜҘж–ҮжІЎжңү收иҝӣгҖҠйӮ“е°Ҹе№іж–ҮйҖүгҖӢпјҲе®ҳж–№и®ёеӨҡеҮәзүҲзү©е®Ңе…ЁдёҚжҸҗйӮ“еҸҚеҸізҡ„и§’иүІпјүгҖӮжҷ“еҶңд№ҰдёӯйҖҸйңІпјҢйӮ“зҡ„й«ҳеҚҮдёҺйҷҲдјҜиҫҫдёҚж— е…ізі»гҖӮеҸҚй«ҳеІ—ж–—дәүеҗҺпјҢдёәеӣўз»“иҘҝеҢ—еҗҢеҝ—пјҢжҜӣжіҪдёңеҗ‘йҷҲи°ҲеҲ°и°ҒжҺҘжӣҝй«ҳеІ—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иҜҙйӮ“е°Ҹе№іжңүдёҖзҜҮи®ІзҫӨдј—и·Ҝзәҝзҡ„ж–Үз« еҶҷеҫ—дёҚй”ҷпјҢд№ҹеңЁиҘҝеҢ—е·ҘдҪңиҝҮпјҢд№ҹжңүеҠҹеҠіпјҢеҸҜд»Ҙеӣўз»“иҘҝеҢ—еҗҢеҝ—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дёӯеӨ®е°ұи°ғйӮ“дёәдёӯеӨ®з§ҳд№Ұй•ҝгҖӮйӮ“еҲ°дёӯеӨ®еҗҺпјҢйҷҲеҸҲеҜ№жҺЁиҚҗйӮ“жңүдәӣеҗҺжӮ”пјҢи§үеҫ—йӮ“жһ¶еӯҗеӨ§пјҢеҫҲдёҚжҳ“е•ҶйҮҸй—®йўҳгҖӮ
дә”д№қе№ҙеәҗеұұдјҡи®®еӣ еҪӯеҫ·жҖҖдёҖе°ҒеҶҷз»ҷ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дҝЎпјҢиҖҢжү“дәҶдёҖдёӘеҪӯй»„еј е‘ЁеҸҚе…ҡйӣҶеӣў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д№ҹеңЁеұұдёҠгҖӮжү№еҪӯд№ӢеүҚпјҢд»–еңЁжҜӣжіҪдёңйӮЈйҮҢзңӢиҝҮеҪӯзҡ„дҝЎпјҢ并еҪ“жҜӣжіҪдёңйқўпјҢиөһжү¬дҝЎеҶҷеҫ—дёҚй”ҷпјҢй—®жҜӣжіҪдёңжҳҜеҗҰеҪӯиҮӘе·ұеҶҷзҡ„пјҹжҜӣжіҪдёңиҜҙжҳҜзҡ„пјҢгҖҢд»–иғҪеҶҷгҖҚгҖӮдёҚж–ҷеҮ еӨ©еҗҺжү№еҪӯејҖе§Ӣ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д№ҹиў«жүЈдёҠеҸіеҖҫеёҪеӯҗгҖӮйҷҲеҒҡжЈҖи®ЁпјҢ并дёҚеҮҶеҸӮеҠ дјҡи®®пјҢжңҖеҗҺжҜӣжіҪдёңиЎЁзӨәеҮ дёӘз§ҖжүҚиҝҳиҰҒз”ЁпјҢйҷҲеҫ—д»ҘиөҰе…ҚгҖӮдјҡеҗҺеҲҳе°‘еҘҮжүҫйҷҲи°ҲиҜқпјҢжҠҠйҷҲйғҪиҜҙе“ӯдәҶгҖӮеҗҺеҸҲз”ұеҪӯзңҹеҮәйқўиҰҒйҷҲеҶҷж–Үз« жү№еҪӯеҫ·жҖҖгҖӮйҷҲдҫҝеңЁ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еЁҒжңӣе’ҢеҺӢеҠӣдёӢгҖҢиҰҒз”ҡд№Ҳз»ҷз”ҡд№ҲгҖҚпјҢеҶҷдәҶжү№еҪӯж–Үз« гҖӮдҪҶйҷҲиҜҙж–Үз« е®Ңе…ЁжҳҜжҢүдёӯеӨ®йўҶеҜјиҰҒжұӮеҶҷзҡ„пјҢ并з»ҸжҜӣжіҪдёңдәІз¬”дҝ®ж”№гҖӮ
жҷ“еҶңд№ҰдёӯеҜ№иӢҘе№Іе…ҡеҸІи‘—дҪңжҸҗеҮәејӮи®®гҖӮеҰӮжқҺй”җзҡ„гҖҠеәҗеұұдјҡи®®е®һеҪ•гҖӢиҜҙдјҡи®®зҙ§еј ж—¶гҖҢиҝҷдҪҚиҖҒеӨ«еӯҗиәәеҖ’иЈ…з—…пјҢдёҚеҸӮеҠ дјҡи®®гҖҚзӯүпјҢиҖҢй«ҳж–Үи°Ұи‘—гҖҠжҷҡе№ҙе‘ЁжҒ©жқҘгҖӢе’ҢеҸ¶ж°ёзғҲзҡ„гҖҠйҷҲдјҜиҫҫдј гҖӢдёӯеҜ№йҷҲдёҺжһ—еҪӘе…ізі»зҡ„жҸҸиҝ°йғҪжңүеӨұе®һд№ӢеӨ„гҖӮ
йҷҲдјҜиҫҫжҷҡе№ҙж„ҹж…ЁпјҡвҖңжҲ‘зҡ„дёҖз”ҹжҳҜдёҖдёӘжӮІеү§вҖқ ...пјҢвҖң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зҠҜдәҶеӨ§зҪӘзҡ„дәәпјҢеңЁвҖҳж–Үйқ©вҖҷдёӯпјҢжҲ‘ж„ҡи ўиҮіжһҒпјҢиҙҹзҪӘеҫҲеӨҡпјҢвҖҳж–Үйқ©вҖҷжҳҜдёҖдёӘз–ҜзӢӮзҡ„е№ҙд»ЈпјҢйӮЈж—¶еҖҷ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еҸ‘з–Ҝзҡ„дәәгҖӮжҲ‘зҡ„дёҖз”ҹжҳҜдёҖдёӘжӮІеү§пјҢ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жӮІеү§дәәзү©пјҢеёҢжңӣдәә们д»ҺжҲ‘зҡ„жӮІеү§дёӯжұІеҸ–ж•ҷи®ӯвҖҰвҖҰвҖқ
еҝҸжӮ”д№ӢдҪҷ
жҷҡе№ҙйҷҲдјҜиҫҫеңЁжҺҘеҸ—дҪң家еҸ¶ж°ёзғҲйҮҮи®ҝж—¶пјҢжӣҫдёҚиғңж„ҹж…Ёең°иҜҙпјҡвҖң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зҠҜдәҶеӨ§зҪӘзҡ„дәәпјҢеңЁвҖҳж–Үйқ©вҖҷдёӯпјҢжҲ‘ж„ҡи ўиҮіжһҒпјҢиҙҹзҪӘеҫҲеӨҡпјҢвҖҳж–Үйқ©вҖҷжҳҜдёҖдёӘз–ҜзӢӮзҡ„е№ҙд»ЈпјҢйӮЈж—¶еҖҷ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еҸ‘з–Ҝзҡ„дәәгҖӮжҲ‘зҡ„дёҖз”ҹжҳҜдёҖдёӘжӮІеү§пјҢжҲ‘жҳҜдёҖдёӘжӮІеү§дәәзү©пјҢеёҢжңӣдәә们д»ҺжҲ‘зҡ„жӮІеү§дёӯжұІеҸ–ж•ҷи®ӯвҖҰвҖҰвҖқ
дёҚд»…д»…жҳҜеҝҸжӮ”пјҢз»ҸиҝҮзӣ‘зӢұз”ҹжҙ»зҡ„йҷҲдјҜиҫҫпјҢзЎ®е®һжҖқиҖғдәҶеҫҲеӨҡпјҢд№ҹжғійҖҸеҪ»дәҶеҫҲеӨҡгҖӮ
еңЁдёҺе‘Ёжү¬и§ҒйқўеҗҺ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жӣҫе°Ҷд»–зҡ„дҪңе“ҒгҖҠжұӮзҹҘйҡҫгҖӢжүҳд»ҳз»ҷгҖҠиҜ»д№ҰгҖӢпјҢдәҺ1982е№ҙ第10жңҹеҸ‘иЎЁ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иғЎд№”жңЁд№ҹжү№зӨәе°Ҷе…¶гҖҠи®ӨиҜҶзҡ„жёҗеҸҳдёҺзӘҒеҸҳгҖӢеҸ‘иЎЁдәҺиҫҪе®ҒзңҒгҖҠзҗҶи®әдёҺе®һи·өгҖӢ(1983е№ҙ第2жңҹ)гҖӮе…Ғи®ёе°ҡеңЁдҝқеӨ–е°ұеҢ»зҡ„вҖңзҠҜзҪӘеҲҶеӯҗвҖқе…¬ејҖеҸ‘иЎЁеӯҰжңҜж–Үз« (иҷҪ然зҪІз¬”еҗҚ)пјҢиҝҷдјјд№ҺжҳҜвҖңжі•еӨ–ејҖжҒ©вҖқпјҢдҪҶйҷҲдјҜиҫҫдёҚиҝҷж ·жғігҖӮд»–иҜҙпјҢвҖңеңЁзӢұдёӯеҶҷдёҚж¶үеҸҠзҺ°ж—¶ж”ҝжІ»зҡ„еӯҰжңҜж–Үз« иҖҢеҫ—еҲ°еҸ‘иЎЁпјҢеңЁдё–з•ҢеҫҲеӨҡеӣҪ家并дёҚйІңи§Ғ;и§Јж”ҫеүҚйҷҲзӢ¬з§Җиў«еӣҪж°‘е…ҡж”ҝеәңеҲӨдәҶеҲ‘пјҢеҪ“然д№ҹжҳҜиў«еүҘеӨәдәҶе…¬ж°‘жқғзҡ„пјҢйҷҲзӢ¬з§ҖеңЁзӢұдёӯеҶҷзҡ„гҖҠе®һеәөеӯ—иҜҙгҖӢгҖҠиҖҒеӯҗиҖғз•ҘгҖӢзӯүж–Үе°ұжӣҫеңЁгҖҠдёңж–№жқӮеҝ—гҖӢеҸ‘иЎЁгҖӮвҖқ
еҜ№дәҺе‘Ёжү¬еҶ’зқҖйЈҺйҷ©дёҺиҮӘе·ұи§Ғйқў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жҳҜеҝғеӯҳж„ҹжҝҖзҡ„гҖӮз”ұжӯӨд»–д№ҹдә§з”ҹдәҶдёҖдәӣж„ҹжғігҖӮд»–еҜ№е„ҝеӯҗйҷҲжҷ“еҶңиҜҙпјҡвҖңйҷҲзӢ¬з§Җиў«е®ЎеҲӨж—¶пјҢд»–ж—©е№ҙз•ҷж—Ҙж—¶зҡ„еҗҢеӯҰз« еЈ«й’ҠеҮәеәӯдёәд»–иҫ©жҠӨвҖҰвҖҰж•ўдәҺдёәеӣҪж°‘е…ҡзҡ„ж•ҢдәәйҷҲзӢ¬з§Җиҫ©жҠӨпјҢжҳҜеҫҲдёҚе®№жҳ“зҡ„гҖӮеҗҺжқҘйҷҲзӢ¬з§ҖеқҗзүўпјҢиғЎйҖӮзӯүиҝҳеҲ°зӢұдёӯзңӢд»–гҖӮзҺ°еңЁйқ©е‘ҪиғңеҲ©дәҶ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дёҖж—ҰжңүдәӢпјҢеӨ§е®¶е°ұйғҪе…ӯдәІдёҚи®ӨпјҢиҝҷдёӘйЈҺж°”е®һеңЁдёҚеҘҪгҖӮвҖқ
笔иҖ…еҫҲе…іеҝғпјҢдҪңдёәи·ҹйҡҸжҜӣжіҪдёңй•ҝиҫҫ31е№ҙзҡ„ж”ҝжІ»з§ҳд№Ұ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еҲ°еә•жҳҜеҰӮдҪ•иҜ„д»·жҜӣжіҪдёңзҡ„гҖӮзҝ»йҳ…з”ұе…¶еӯҗйҷҲжҷ“еҶңеҮәзүҲзҡ„гҖҠйҷҲдјҜиҫҫжңҖеҗҺеҸЈиҝ°еӣһеҝҶгҖӢпјҢйҮҢйқўи®°иҪҪдәҶеҫҲеӨҡзҲ¶еӯҗй—ҙеқҰиҜҡзӣҙзҺҮзҡ„дәӨи°Ҳ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дёҚжӣҫеҜ№жҜӣжіҪдёңжңүеҚҠеҸҘйқһи®®гҖӮдёҚз®ЎжҖҺд№ҲиҜҙ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еңЁеӨ©зҝ»ең°иҰҶзҡ„1970е№ҙд»ЈпјҢиҝҳжҳҜеңЁжҜӣжіҪдёңе·Із»ҸйҖқдё–еӨҡе№ҙзҡ„1980е№ҙд»ЈпјҢйҷҲдјҜиҫҫйғҪжІЎжңүзүҮиЁҖеҸӘиҜӯеҹӢжҖЁжҜӣпјҢиҷҪ然他жңүи¶іеӨҹзҡ„зҗҶз”ұеҖҫеҖ’иӮҡеӯҗйҮҢзҡ„вҖңиӢҰж°ҙвҖқгҖӮ
1980е№ҙеҶ¬еӨ©пјҢдёҖзәёиө·иҜүд№ҰйҖҒеҲ°иў«е…іжҠјеңЁз§ҰеҹҺзӣ‘зӢұзҡ„йҷҲдјҜиҫҫжүӢдёҠж—¶пјҢиҝҷдҪҚ76еІҒзҡ„иҖҒдәәе“ӯдәҶгҖӮд»–иҜҙдәҶдёҖеҸҘеҸ‘иҮӘиӮәи…‘зҡ„иҜқ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жҜӣдё»еёӯиҝҳеңЁпјҢиҜҙдёҖеҸҘиҜқе°ұеҘҪдәҶгҖӮжҲ‘дёҚиҪ»жҳ“жөҒжіӘпјҢд»ҠеӨ©жҲ‘е“ӯдәҶпјҢзҺ°еңЁжІЎжңүеҠһжі•дәҶгҖӮвҖқ
зӣҙеҲ°йӮЈдёҖеҲ»пјҢд»–иҝҳжҳҜе°ҶиҮӘе·ұзҡ„е‘ҪиҝҗпјҢдёҺжҜӣжіҪдёңзҙ§зҙ§иҒ”зі»еңЁдёҖиө·гҖӮ
(иө„ж–ҷж‘ҳиҮӘеҸ¶ж°ёзғҲпјҢйҮ‘й’ҹ пјҢйҷҲжҷ“йҫҷгҖӮеҺҹж–Үз•ҘжңүеҲ иҠӮ)




